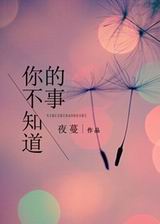写作的事-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1。“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
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备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像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像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像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鄙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崇的将是和解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须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
所以我想,文学也该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了,它既然是人学至少我们应该对“征服”、“大师”、“真理”之类的词汇重新定义一下。至少我们在“气吞山河”之际应该意识到我们是自然之子。至少我们在主张和坚持一种主义或流派时,应该明白,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当父性的英雄,排斥众生独尊某术,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会破坏了场,同时使自己特别难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体的真理)是承认这种多元——人总不能自圆其说,这是悖论的魔力。
12。所谓“贵族化”,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义的,一种是褒义的。
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类的生活问题都已解决,因而以为天下都已温饱,不再关心大众的疾苦乃至社会正义,这当然是极糟糕的。
一群人,肉体的生存已经无忧,于是有余力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甚至专事探讨人的终极问题,这没什么错,而且是很需要的。
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他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
精神问题或人的终极问题,势必比肉体问题或日常生活问题显得玄奥。对前者的探讨,常不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甚至明显地脱离实际,这很正常,绝不说明这样的探讨者应该下放劳改,或改弦更张迁就某些流行观念。
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
“贵族化”一词是借用,因为过去多半只是贵族才不愁吃穿,才有余暇去关注精神。现在可以考虑,在学术领域中将“贵族化”一词驱逐,让它回到原来的领域中去。
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
我只是想,不要把“贵族化”作为一个罪名来限制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怀,也不要把“平民化”作为较少关怀精神生活的誉美之词。这两个词,不该是学术用词。至少这两个词歧义太多,用时千万小心,我想,文学更当“精神化”吧。
《写作的事》 第二部分“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3)
13。乐观与悲观。
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
见了这种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与哀叹再无其他作为——这种悲观是傻瓜悲观主义。信奉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真是惨极了,他简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也已经说过了,人可以把困境变为获得欢乐的机会。
人的处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内在的乐观和悲观,对此稍有不承认态度,很容易就成为傻瓜。所以用悲观还是乐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毫无道理的。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恰恰说明它没有沾染傻瓜主义。当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乐观和悲观,变作艺术,来观照、来感受、来沉思,人便在审美意义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计较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他谛听着人的脚步与心声,他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这儿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着敬畏的骄傲)。所以,乐观与悲观实在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领域中去吧。
况且,从另一种逻辑角度看,敢于面对一切不正是乐观吗?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观。这样看来,敢于写悲观的作品倒是乐观,光是叫嚷乐观的人倒是悲观——悖论总来纠缠我们。
《写作的事》 第三部分宿命的写作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
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
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
借助电脑,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其中有这样一段:“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卖文为生已经十几年了,唯一的经验是,不要让大脑控制灵魂,而要让灵魂操作大脑,以及按动电脑的键盘。
《写作的事》 第三部分获“庄重文文学奖”时的书面发言
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
丰衣足食、移山填海、航空航天,总之属于经济和科学的一切事,都证明人类“确实有办法”。但是,比如痛苦不灭,比如战争不停,比如命运无常,证明人类也常常处于“实在没办法”的地位。这时我们肯定会问:我们原本是想到哪儿去?我们压根儿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问题是穷人也是富人的问题,是古人也是今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科学还悠久比经济还长远,我想,这样的发问即是文学的发源和方向。
但这样的发问,仍是“实在没办法”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否则这发问就会有一天停止,向哪儿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一旦消失,文学或者人学就都要消灭,或者沦为插科打诨式的一点笑闹技巧。
有终极发问,但无终极答案,这算什么事?这可能算一个悖论: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发问即是答案。因为,这发问的过程,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
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
《写作的事》 第三部分熟练与陌生
艺术要反对的,虚伪之后,是熟练。有熟练的技术,哪有熟练的艺术?
熟练(或娴熟)的语言,于公文或汇报可受赞扬,于文学却是末路。熟练中,再难有语言的创造,多半是语言的消费了。罗兰·巴特说过:文学是语言的探险。那就是说,文学是要向着陌生之域开路。陌生之域,并不单指陌生的空间,主要是说心魂中不曾敞开的所在。陌生之域怎么可能轻车熟路呢?倘是探险,模仿、反映和表现一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