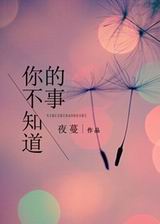���ҵ���-��1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һ���Ǻü������Ӳ��ܳ�һ���Ƚ��ܸɵ��ˣ��������вŸɵ�ũ��Ż��������뷨����������
�����������ң�ũ�����ڵ�����һ����ʲô�����˵�����������ϻ���ʶ�������˼ҵ�����������ѵ�֪���Լ��ڳ��������µ�һ�ж���Ϊ���˵ģ��Ծ��ذ��Լ������ڡ����ˡ�֮�¡������һλŵ������ѧ��������������������ң�����һ����̫�ˣ�����ս����ʱ�¹��˹ؽ�����Ӫ��������Ʒ��������Ƕβп��������ڼ���Ӫ��иɻ�ɻ�о��־;��֣��˼���û��ʲô˼����ʶ�����������ܻ������뷨��ֻ�������ܱ���������ܶ�����й�ũ����Щ������������˵���ݡ���ʹ���Ե��������������
��������������Щ�귢���ı��Ҳ�ƺ���ũ���ء���ʵ���������������ǻ��������ܻݣ����義����ͨ���Ժ���ũ��о�����һЩ�ô������ǵ���ͷ�������ˡ������ƶȲ����Ͻ���ũ��о�������Щ�仯������Ҳ��������Щ���顣
��һ�����������ֲβ�ķ羰2003�꣬һ������������4��
����������������ij��У����й��������ij��С����Ϻ��ͱ�������ǿ��ij���һֱδ�ܸ����ң������ϵ�ũ����ӡ��Ȼ�dz�ǿ�ҡ���������
�����������ڳ��еĸ�¥����֮����Ըо����ܶ��ʽ��������������Ѿ�������·����ͣ���ˣ�����ЩǮ����������ũ��ȥ����ũ��������ҪǮ�ĵط���ʱ�³��������һ����ҵ�Ǯ��û�У�����Ϊʲô����������
���������������壬ͨ����ѧ�߳���壬�ı��Լ����˵Ĵ����30�����ˡ����д������سǡ����ѧУ���飬�����˹��ҵķ��롣�ܹ��ߵȽ���������10�����ң��е��ں��ݡ��ϲ����Ž��������ߵ������ľ�����һ������Ů�ܹ�����ũ������ݣ���������������ũ��ļ�ͥ����������һ���ܹ��ٵ����顣��������
�������������ҵ���ͷ��������ֵܽ��ã���������Ľ�Ŀ�������˵���������dz����ˣ��������������ܺã������ǻ��������������˵���Ƕ��Ǵģ�ֻ�������ڱ������Ļ��������Ǻ�һЩ���������Ϸ���������һЩ�����������������Ƕ��Ǵ�������Ȼ�������ϱ������ϣ��������������ֻҪ���������ƣ����ӵ�����Ƹ�����Դ����һ������ʲô�������ٻ���ҽ�Ʊ��ϡ�������Զû�п���������Щ��Դ�����ǻ����ھ���֮�У�������ʲô�ֻ�����������ĥ�ѣ��ܿ���Ҫ�������𡭡���������
���������Һ����ǽ�̸��Щ�����ʱ��ȷʵ��һ�ֱ��ѵĸо��������Լ�û�ܰ�������ʲô������Խ����Ľ�ҵ������Խ�Ǹо������ݡ���������
����������������ij��У����й��������ij��С����Ϻ��ͱ�������ǿ��ij���һֱδ�ܸ����ң������ϵ�ũ����ӡ��Ȼ�dz�ǿ�ҡ���������
����������������ôЩ�꣬�ҵ������ιʹ����ú�������û��һ���ο͵����ܸУ�Ҳû��һ����ѧ�ļ��У���һ��ũ�������ļ����£��е���Ω��һ��������������ı��ϣ��Ҹ����ź��������������������������¹�����ũ��ĺ�ˮ��Ѫ�ᣬ���ߣ����ǵ����˶���ũ���Ѫ��֮���ŴӴ���Զ�ĵط������������������ɽɫ�﹩�ʹ����������ֵġ��ڹʹ�����Ҳ�ǻ���һ�ּ���������һ�����������һ���شX�ֵĴ���ʯ���Ҵ̼���������������˶�������˵�������Ȼ�����˵��㽭ȥ��̼ӹ�������֮�����˻ر��������Ҳ�˵�������;�У����кܶ�ũ��Ϊ֮���˻������ˣ���Ϊ�������һ��̣�ũ��Ҫ�����ٿ�����˰�����϶��ٰ������յ����ۣ�������Ŀ�У��ý���������Ŀ�ĺܶ���ʷ�Ļ��Ų��������ﳤ�ǡ�����ٸ��С���������ߵ�һ��������ˣ���ʵ����ũ��İǻ���һ��˵������������
�������������������һֱ����룬������˽����Ƚ��٣���ν����ײ�����������ء����ڳ����С��ס��ʱ��ÿ�ο�����̫̫������Ů��ǣ��һ��С�����䣬�Ҿ������������һ��С�����������������˽���������һ��ũ��Ŷ�������һ�������и��顢�������壿ʱ��������Ϊʲô������Խ������ԵĹ�ͨ��������Щ��Ǯ������ܰ��Լ�����IJ���������ת�Ƶ���ṫ����ҵ���������Ƕ��������洦�������ǵ��Ҹ�����Ҳ��̫ƽ�𣿡�������
��������������װ�Ŵ�����ô��¶�����������ǵ����ˣ���˵�ҿ����������������������ʲô���ܣ����ڳ���μӸ�����Ŀ�ľۻᡢ��ᣬ����һ�����Ե���ǧ��Ǯ���ٱ�ʱ���ϵ�Ȼ�ö���Ц�ݶ��˼ұ�ʾ��л������ȴһ�����ʹ���⼸ǧ��Ǯ�ø�ũ���������ǽ�������������ѣ��һ�����������ܳ�һ��ʱ�䣬ֱ����������ٷ���������Ž�������������
���������������ũ����۹����������������ʱ�����л���С��������ҿ϶��Ƿ��еġ��������־�������Լ��������������۹���Ҫ����ˡ�ũ������˦����ôԶ�����䵽������һ����������ij����ʷԭ����ɵģ����й�������ʷ�����������㣬����Ҫ������Ĵ��ۣ���Ҫ��������ʱ�䡣���ң��ڵ����ٲ���������������Ҳ���ᡰ�����顱��ֻ���г����ã��Լ�����һ�����ˣ�һ���ֵ����ȸ�������������Χ�£�Ҳ������Ҫ�������˶���ũ��һ�������ӡ���������
������������������ȥ���������������������ʺš����������ˡ�����������
��������1949�꽨�������й���Ȩ���ǴӸ���һƬ�������忪ʼ�����ģ�Ϊ��������ӵ��ɽ��ǰ�ͺ���Ѫɳ���ģ����Ҳ��ǧǧ�����ũ������֮��Ϊʲô�ܿ���ȡһ��������ũ������Ϊ���۵��ι����ԣ���������
�������������ڣ����ڳ��еĸ�¥����֮����Ըо����ܶ��ʽ��������������Ѿ�������·����ͣ���ˣ�����ЩǮ����������ũ��ȥ����ũ��������ҪǮ�ĵط���ʱ�³��������һ����ҵ�Ǯ��û�У�����Ϊʲô����������
����������������ϡ������Ϻ�ǿ�ҵع�עũ��˼ά��ũ����һ��ġ����߳�ũ����ô���꣬ȴ����û��Ϊũ��д��һ���飬������û��Ϊũ��˵�����仰����Ȼ����ũ������ľ��������ҵĴ������źܴ�Ӱ�죬���һ�û�����ũ����һ�����Ⱥ�������д�������������
���������յ�����ʱ�����뱱����ѧ����ϵ����Ǯ��Ⱥ����һ���棬��������һ����ũ������������ˣ���˵������������ũ�������ѧ�ߣ���ϲ������Щ���ӵ��˴�������Ҳ����һ�����⣬������Щ�˶�����ʵ������ѧ������������ũ������Ҳ�к�������飬������ѧ������������Ŀ����չ�ķ���ȴ����û��һ������ũ���йأ����о�����ũ�������йء�����γ�ǿ�ҷ�����ǣ������о�ũ������ģ����Ǿ��бȽϸߵ���������͵�λ�ij����ˣ����Ϻ��IJܽ�������д�ˡ��ƺӱ��ϵ��й����������Ҷ��о�����ũ�������ר��ѧ�ߣ����������о��ķ���ľ������⣬�Ҷ���������Ȼ���Ͼ����ǰѹ�ע��Ŀ��Ͷ����ũ��������
����������ʱ����û�ܻش��������⣬����Ҳû����ʽ�ش�Ǯ���������������������ҵ���ԭ��һ���DZ����ԭ��һ���˽��������Ժ�Ҫ����������Ƶ���Ϸ��������ת������ά���Լ������ơ��ϼ���������ʲô���⣬����밴��Ҫ��ȥ�������ܵõ����ѣ������ſ���ı��������ǰ����ũ������һֱ���ڹ��ҵĹ�ע֮�У�Ҳ���������ǽ����ⷽ����о�����ũ�������ѧ��ֻ��ͨ���������������Ŀ��⣬�������������Դ��ѧ����λ������Լ���ǹƥ���ظ㡰��ũ�������о�������û������������Ҳ���ܺ���ı������������
���������ڶ���ԭ���������εġ���ũ��������ˣ�����ũ�����������ɵ�ʹ��Խ����Խ�����ĵ������������ӡ�ǡ�һ������������صĶ������Dz���ȥ��ԣ�����˵һ����û������ȥж���Լ�������Ų��µIJ��֡�������Щ��ũ�忼ѧ�������ˣ�����һ��һ�㲻�����������飬��Ϊһ�ĵ�ũ�壬���˾�ɥ������ʹ�����Ǽ����������ũ�����״������ô���أ�ֻ�ð��ⲿ�����ݷ���������Ҳ��ҿ����ƺӱ��ϵ��й��������飬Խ������Խ����˺�ѣ������Ҳ��ҿ��ܹ�ƽ����д�ġ��椡�һ��������ʹ���һ���������ܹ����ܵġ���ʵ�������ڳ��������Դ��ڼ����ķܶ��У���û���㹻��������������������һҳ����������
���������ҿ�����ũ������Ľ��������Ҫ�ƶ��ϵ��Ƹ����ۣ�Ҳ����ũ���ֵ����������������ϵ�һ�����ϸ�������������Ҫ���ǿ��ⲿ�Ĺ��գ����ǿ������Ĵ�������ȥ��ƶ�¸�������˵����������ȥ���������Լ�����������
����������ƽ���߷�Ħ��û���κ���������һ���ھͳ����ˡ���ũ�����⡣Ѫ�����ʳ���������Ѫ������һλ����̵��ǻ���ʶ�����Ƶ�ѧ�ߡ����ң������������ڳ������ũ����۹⣬������ȴ�ֱ����������˵�˫�����Σ��������ľ�������ܣ��������������IJ�ƽ�������Ŷ�����Ҳ��ͬ�С���������
������������ǰ��д�µģ��һ���˵���ǡ�����������
����������Ħ��̸�������ᵽ���Ƶ�ԭ��ũ���й��������������ų⣬��Ȼ�����ũ��ƶ��������Ҫԭ����Ҫ����ũ�����յ������ܶ��ԣ�����Ч��·���϶����ƶȱ����ѱ������ڰ���ũ����������������ɡ���Ӫ���ɻ�������ũ������Ϊ���������й��в�������ũ�������ֲ������������Ƶ�ԭ��������
������������һ��������Ҫũ���Լ��Ծ���Ҫ�����Լ������Լ���һ��ũ��������������Լ��ˡ����������ũ������Լ��г����÷���ʵ����Ϊ�й�ũ��չʾ��δ��ũ�������羰�����ݵ�ũ�������й��͵������Լ��IJ���һ��������ȥ�������������ӣ��ڸĸ↑���������й����ʤö�١���������
����������ˣ��ҿ�����ũ������Ľ��������Ҫ�ƶ��ϵ��Ƹ����ۣ�Ҳ����ũ���ֵ����������������ϵ�һ�����ϸ�������������Ҫ���ǿ��ⲿ�Ĺ��գ����ǿ������Ĵ�������ȥ��ƶ�¸�������˵����������ȥ���������Լ���
�ڶ�����������֯�������������գ�1��
����������ƽ�����գ������ǡ��˽ܵ��飬�ﻪ�챦��������������
�������������Ǹ����μҡ����¼ҵĶ��ʡ�ݣ���������������ʷ�ľ��У�����ʱ������㹫��Ϊ�����һ�������Ĺ��٣�ս��ʱ��������������ڽ�����������ķ�������ĩ��������ʱ�۲Ŵ��Ե�κ��۲ܲ٣��Լ���褡�³�ࣻ�δ����������¡�����ǧ��İ�����Ԫĩ�����������ر����������ĺ�������壬��������Ԫ谻�ˮ���㣬����ƫ�棬�ճ������Ŀ����ʵۣ��峯�̷���䣬�й����Ρ�������̨��һ֧��Ҫ����������ϵ��������Ϊ����������������˶��ķ�����֮һ����Ϊһ��ĺɫ���ص��л��Ź�������Ͻ���������;����ν�龫���ǣ��ٸ���У�������������������ܡ��ĺϷ��˶���������ϵ����Ҫ����Ժ��������������з����顢�����С������͡������˵ȣ������������������г¶��㡢�����顢���ũ�������¡�Ƥ��������ѧ�ǵ���ʮλ�����졭����������˵�������������������ϣ�Ϊ�ҹ���ǧ��������ʷ�����ģ������Ӣ�ۣ��������ԣ�Ϊ�����ǧ������ʷ�Ĵ���������������
���������Ļ��������ϣ�����������ˮ�����������dzۡ����ӡ�ׯ�ӳ����ڱ����к�һ�����Ϊ�й��Ŵ���ѧ�Ĺ��硣����ĩ�꣬���ݳ��ˡ�ҽʥ��٢�����Ժܲ١���ا����ֲ���ӣ�ʷ�ơ��������ܡ������й���ѧʷ��������Ҫ��λ��κ��ʱ����������Ψ�Ҷ���ġ��������͡��У����������������档�������ɢ�ķ�����ͩ���ɣ�С˵����д�ˡ�������ʷ�����⾴����������������������緶Χ����Ӱ��Ĵ�ʦ��ѧ�ߺ����Ļ��˶�����������������ʿ�����ź�ˮ������ȡ�����罡����DZ������֪���Ʊ��硢�����ˡ�������������Ϸ�Ӣ�������ġ��˼��ȡ��������������Ĵ�հ��������չ�����Ƶľ��类��Ϊ���磬��÷Ϸ�೪���ϱ��������й������ݺ긻�Ļ����Ļ�����ػ�ѧ����ѧ�ȼ������Ϊ�����й�����ط���ѧ֮һ������ʱ������������ԻΪ�������̣��ѳ������ݵ�����̺���ⱦ������Ϫ�˺�ѩ�Ҹ��������ġ��춥���ˡ������ں���Ԫ���ֽ���լ�Ķ�ʢʱ�ڣ��Ҳ���4��000�������Ϊ��͢�������һ�룬��ν���ɵй�����ʹ���˽���������Ҳʱ�����֮�ȣ��й���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