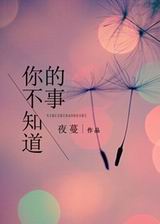国家的事-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浙江人有流动的习惯,喜欢走街窜巷做些“鸡毛换糖”的小本生意,像义乌以前就有换鸡毛的,把回收的鸡毛做成鸡毛掸子去卖。“敲糖帮”的组织管理复杂而又严密,既有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又兼顾现代管理的不少理念,为今天的义乌人管理现代小商品经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义乌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县城,开集市还是逢单开或者逢双开。但现在的义乌足以让全国刮目相看,凡是做小商品批发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有几十个国家的贸易组织在义乌有常驻机构,那里集散了全国各地的小商品,但主要还是义乌本地的商品。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打衬衣的价格便宜得简直让你没法想像,平均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想想连买布也不止这点钱,但在那里就有那么便宜。上海城隍庙的很多小商品都是从义乌进的货。现在义乌干脆在上海福佑路又建了一家小商品市场,它在上海都能占有市场,在全国就更不用说了。义乌还有一个老板私人投资几千万美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建了一个小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这正是浙江人(尤其是农民)自主谋生冲动和自主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中流动最典型的当属温州人,他们甚至走到了国外,在整个欧洲都有“温州帮”。温州人可以凭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制品生存,把这些东西卖掉以后,买张飞机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竟在那里做了老板。
有学者对北京的“浙江村”作调查,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浙江农民的土地依赖意识已经急剧减弱,尽管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存还抱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离开田地做工、经商、上大学表现了坚定的意向,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甚至做好了随时远征、另行开辟新天地的准备。问卷结果显示,“浙江村”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对“农民的孩子应以种田为本”的说法持十分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总数的7%和15%,而不太赞同的和很不赞同的却分别达到35%和21%。“浙江村”的农民很愿意和愿意到一个条件差、风险大,但机会和挣钱多的地方去发展的,分别高达16%和35%。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确实制造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假冒骗”在经济过程中时有发生。乐清县柳市镇产的矿灯漏电,几十万双温州劣质皮鞋在杭州市被当众焚毁,还有假烟假酒假商标等等使“温州=假冒骗”曾被一时传扬。这不仅大大制约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温州的形象。为此温州市委市政府在1994年大力抓了以“质量立市”的全民工程。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3)
有些温州人对此所作的解释却振振有辞。比如说皮鞋,当时温州的皮鞋价格很便宜,别的地方一双皮鞋可能要100多块钱,温州皮鞋则不到20块钱一双,而且样式很好,但是这个皮鞋是纸做的,穿三个月就坏了。那么人家就说温州人怎么卖这种纸皮鞋呢?这不是骗人吗?有些温州人是这样解释的,你花100多块钱买一双皮鞋可以穿一年多,同样花100多块钱可以买5双甚至10双我们的皮鞋,而且可以经常换式样,等于是天天穿新皮鞋,成本也降下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
从这“歪理”中却可以看出部分温州人的一种快速消费的理念。在早期原始积累的时候,他们的生产观念、消费观念包括产品设计等一整套理念都表现出短平快的节奏。等到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现在温州很多企业的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了,产生了很多资产几亿、几十亿的私人企业,这时候他们开始考虑建立品牌了。温州有两个品牌,一个是地方品牌,即温州作为一个地方的品牌,就像谈到葡萄酒就会想起法国一样,温州的电器、皮鞋、打火机现在是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是企业自身的品牌,温州现在有好几家知名企业了。
温州人现在对此看得很清楚。品牌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很多小企业互相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下去了,有些企业则慢慢发展起来了,到了一定的规模它一定会讲究品牌信用,这是恩格斯说过的话。因为对小企业来讲,信用和名誉的意义是不大的,但是大企业就不一样了。这并不是说大企业的觉悟要比小企业高,而是大企业如果卖了质量不好的产品的话,它的损失会很大。具体地说,大企业的生产一般是流水线,流水线的生产质量基本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有意把产品做得不好。假如做得不好的话,那它损失的就不是一双两双皮鞋,而是整个一批产品,这样它的损失当然大,而且把自己的信用损坏了。大企业随着自己的实力逐步增大,名誉、品牌的理念也逐步会成为它财富的一部分 ,此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做人也是这样,穷人是不管形象、身份这些东西的,只有自己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自己的身份,可以说现在的温州人和以前的温州人已经大不一样了。
我们解释温州模式的时候,一是由于人多地少,二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能工巧匠多,三是人口的流动性,加上特殊的地缘文化,温州人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就是具有很强的地域观念,最直接的表现即其语言的特殊性。
温州以前是崇山峻岭,与外界相对分隔,居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其他人听不懂。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当时我军内部联系的密码被越军破译了,为了救急,前线部队调用了所有温州籍的士兵当通信员,直接用温州话通话,对方硬是破译不出来,所以说他们的语言很特殊。温州话连杭州人都听不懂,现在的杭州话是北宋南迁到临安建立南宋王朝以后,和当时的本地语言混合而成,它的语言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北方语言组成的,和温州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因此浙江人自己大都听不懂温州话。
温州人在内部是很讲信用的,这和中国农业文明中的地缘、血缘亲情有关系,他们非常看重乡亲的关系,互相之间一般都肯帮忙。一个地方只要到了一两个温州人,而且只要有商机,无须多久便会有几十、几百个温州人来此共谋发展。他们内部很讲诚信,通过互相协作产生民间金融组织,有些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却可以调动很多很多的资金。在民间的工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国有银行只能支持国有企业不可能支持民间企业的时候,温州民间就已经在自发地筹资扩大再生产,其间虽经几次取缔和清理整顿,但一直存在,至今仍然十分活跃。
温州人还有一点特性就是对财富的认识,我看这是中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所不具备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文革”时候,有一年过年他和妈妈在菜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这时他妈妈说另外还要买点东西,就叫他在街角上稍等一下。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来,这个人也是来买鸡的,但是菜场的鸡已经卖完了。他就对我这个朋友说,能不能把鸡卖给他,并出了一个高价。我的朋友当即就把鸡卖给他了。当时我的这位朋友还是刚上小学的年纪,这是他做的第一笔生意,那时候就知道低价进高价出,这里面有一个价格差,他宁愿放弃对美食的享受也要赚钱。这从一个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来,温州人对钱是怎样一种冲动,钱拿在手上的快感比吃东西的快感有时更重要。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追求是一致比较看重的,而且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很强,他们互相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一般遇到钱的问题会分得很清楚,这个钱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是兄弟之间都会分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开始就对私有产权分得很清楚。
可以这样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眼红人家的财富。假如你拥有了财富,他就会争取比你更富有。以前在《宪法》没有明确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时候,他们有了钱以后,进一步投资又怕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就争相造坟,温州有一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祖坟,他们造坟也是不甘示弱,你造了一个很气派的坟,我就要造一个比你还要大、还要豪华的坟。此外,温州人有钱一般不太炫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还是蛮节俭的。当然,现在温州人很会消费了,温州是全国最敢穿的地方,也是穿得最时尚的地方,他们现在也很讲究吃。
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再一个是市场化,温州在全国都是第一。
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4)
史晋川(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州人的思想是蛮务实的,只要有钱赚,不管干什么,他都能去做,肯吃苦。我去年在纽约呆了一个半月,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呆了一个多月,发现在纽约的唐人街等地方,温州人的势头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要盖过广东人了,很多超市原来都是广东人或者中国其他省市的人开的,但现在那边只要是规模大一点的超市都是温州超市,原来的名称都是叫“香港超市”、“中山超市”、“佛山超市”等等,现在是“温州超市”,还有很多店铺都是温州人开的,而且温州的同乡会在那边势力也是蛮大的,当地华人的报纸经常报道有关他们活动的消息。
我觉得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这个创新温州在全国是第一。在早先,大批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纷纷戴上股份合作制的红帽子。温州的老百姓很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避开与当时的正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温州的老百姓很善于做到这一点。股份合作制的最早出现可能不是在温州,因为台州、山东都说自己是第一家,但是股份合作制大规模地做起来却是在温州。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州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已基本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者说接近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形式。他们搞这个股份合作制就采取了一种让官方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办法,不至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显得太激进。比方说在公司股份合作制的条例里面,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默契的前提下,划出一块不参与利润分配的的公积金,有了这个就可以把这个企业定性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企业了。这块公积金在形式上是大家的,可以界定为每个人有多少,还可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而滚大,但是持有者不参加分红,也不参与决策。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公积金说起来是每个职工都有份,实际上还是在控股的那些人手中,他们将来随时可以抽走这部分资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旦搞规范的现代化企业,只要产权制度一明晰,这块公积金很快被那些事实上的持有者分解掉了,一般的工人说起来是股份合作者,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企业。他们当时把这块公积金包装成一块不能分割的东西,就是为了对外可以说这个企业是集体企业,以一个集体企业的身份站出来官方就好认同了,而且因为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在贷款、征收土地、减免税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所以说温州人不会去与意识形态发生正面冲突,我觉得这是温州人非常聪明的地方。
温州最早都是一些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形式,现在这里面已经成长出一批现代化的企业,像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仁本集团、人民集团、均瑶集团。比如均瑶集团,它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农民包飞机。原来很多航空公司因为票卖不出去,不敢增开航线。王均瑶总裁就提出来由他们公司出钱包航线,最早包的航线是从长沙到杭州。他和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