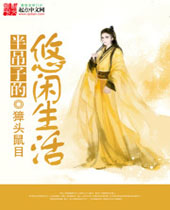С���ӵİ�����-��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ϵ����������εĻ����ϡ�����ʦ��������˹ʡ��Alsace�������DZ���Ӣ��˽��ѧУ���ݵĽ�ѧ����Ч���¹�ѧУ�ĵ����ſη�ʽ����������
����������������������dz���������������ʦ��ƽʱ�������̴����Դ����������ϸ�Ľ���ǿ��ѧ���Ẓ̌�У���������ߣ�Լɪ������Fran�sois��Joseph��Keiffer��������������������Ϊ���Ľ�ѧԭ��ʱ������˹ʡ�ɵ¹�ͳ�Σ������������ڼ��磬�����ܵ���ʿ��Ѱ��ӻ�����������
������������������ʦ�У��������߶���Antoine��Wahl������ѧ���������߶���ʦ���ڵ��ġ���������Ȼ��ѧ����1903�꣬��������и��˲Ʋ����˰�ʥԼ��ѧУ���߶���ʦ�ǰµ����ˣ������İ�С���������롣����ѧ����������������һ��ɽ������Լ������ʴȡ��߶���ʦ��1933���������ʱ����Ȼ���ؽ�ʦ��λ������˵���߶���ʦ�Ĺ�ȥ���൱���ء���ѧ���Ľ����ǣ���ʦ����ʧ������Ȼ��ȻͶ�������硣��������
������������ʥԼ���Ľ�ѧ�ر�ע�ص�����¹��Ļ�����Ҳ��������ʥĦ��˹һֱ�������ӽӴ��Ŀ�Ŀ�����������Ů������Ϊ��Ҫ����ʥԼ��ѧУ����ʦ�ѵ��ﵱ��ĸ�����̣����ǻ��Dz�����ֹ������ʫ���̷����������¹�������ʫ�д���������ս�������С���������
�������������������ѳ������Ʒ�п��Կ�����ֻ��ʥԼ��ѧУ��������������Уʱ�����˵�ӡ��ȴ�������Ӳ������������ᡣ���ܰ�������У��¼�Ѿ���ʧ������ʦ���ǵã����ijɼ����ǵ�ף������������Ŀ�Ҳ���ù�����������
�������������������д������������Լ�����Ʒ�ϣ�����һ����Ϊ����ɡ����ڶг��硣�����ѽű��ĸ�С������ʦ���ȣ�������������Anne��Marie��Poncet���������Ծ��鲢������Ȥ�����¹����ǣ�������һ�ѱ�����������Ůɡ��һ�����������������ɡ������������Ȼ����������ɡ�����ˡ���һλ�����ª��Ů�ӵ���ȡɡ�����ӲŴӰ���������������������
����������������âʱ������������Ϊ����ѱ�������������̬�ȶ�������������������ʥԼ��ѧУ���Ƚ��˽������������ޱ�����������λ���С����ع�ص�ѧ�����������������ᵽ��ʦ�̻�Ŀ��ġ������ڵ�һ��С˵�������ʺ������ᵽʥԼ��ѧУ���龰��������Ϊ���µ������̡�������Ӣ���ſˡ�����˹��Jacques��Bernis����ƽʱ�������ͷ��������ʼ�����һ�죬����˹���������Ρ������µİ�ɫ���ӡ����廳��ʱ���εΡ���������
������������������ҵʮ������ص�ĸУ̽����ʦ����������������д������С�С˵����һ�����ֱ���������ʦ����Ũ����У��������л��Щ����˥�ϡ�����Ȼ���ֹۡ����ˡ�����ʦ���ڡ������ʺ����У���ʦ������ð�շ�������ľ��ʹ��¡������������űȽ�Σ�յķ�����������ѧ˼��IJ��졣��˵����˹������̩�ɺ���ɵ���ѧ����ֻ����Ϊ�����ṩһ�����ۣ���������������ǰ����������������ʱ��ݵ���ѧ�ң������������Ϻ����в�С�IJ�ࡣ���������������ͻ�������ķ��գ���ͻȻ�䣬������ᵽ��У����ϰ�������صIJ���̤��ĸУ���úû�����ɫ��������������
����������������ʱ����ʦ�ó�һƿ�����Ͼƿ������������Ϊ�˲�����λ����ʱ����ż���ѹ�������˹����ǿ��ð����������ʧ����һ�棬������ʦ�������ţ����������鱾��ƽ�������硣��������
��������������ι��ºܿ���ȡ��������ʦ֮����ʵ�ĶԻ����������������������ʦ������Ǹ�⣬��Ϊ��ǰ��ѧУʱ������������������������Ը�Ĺ����棬����ʦ������Թ�ڣ����˻�÷�����˵������֮�⣬��������������
������������ʥԼ���������Թػ��Ļ���ʹ�ð���������Ү�ջ����Ӱ�Լ��游�Ŀ��ơ�1917�꣬������ҵ�������뺣�����������������ܵ����������ʼ�ܵ����ɡ���������
��������������Щ�ı��Ӱ�����Զ���������Ǻ�ʮ�ֻ��Ա���ڴ�ս����ǰ����ʮ�ֻ�Ϊ���ˡ������ṩ�˱��ְ��ĵĻ��ᡣս������ͷ�����£�����Ŀ������ᡢ���顢�Ҿ���徵ľ��¾�ս��Ӫ�ڵķ����˲йٱ�·����ʿ�ص�������ڷ�������ת��Ȼ��ĵ�һվ���ǰ����ԡ������ڵ��ظ���Ӵ���Щ�ٱ�����ɭ����ѹѹ�ij����W�����ˣ����DZ��ٴ�����Ե���������زзϣ���������������ο�������������顣��һ������С������ǵ����оþò�����������������
����������������ӵ�й��һ���֤�顣����Ŀ�������龰��ƽ��û�м�����������������֮һ����ʵ�ϣ�������������Ҳ��ս���в����������Դ��Ժ����������������ܣ�����ʱ�����������������˵�ʹ�࣬���������˺�С������������
������������ս���ڼ䣬����ʥĦ��˹�DZ����Ա�����������飬���һ�������˺ܶ��ˣ�Ȼ���DZ��ڵĹ��������֮��ķ���ȴ������ʹ����ʧ�ˡ������ء������ɣ�1912�꺽��վ��ɵ����У����ĸ����ñ�ӱ����ʪ��˵��ս������ǰ�����ԵĽ������Ͱ���ͬ�䣬������·������ʱ�������������ƺ�����������ү��������ĺ��Ӵ�ഩľ�죬��˰������ϵ�������ƤƤЬ������Ϊ��ҵĻ��⡣�����صĸ����Ǵ����һ����������ˣ���ս֮ǰ��ʥ���������������Ҫ��ͨ����ʱ���DZ�������˻������ѳ�������1914����������˼��٣��������Ҫȥ����վʱ���������ߵ�����IJݽг�����������
������������1918��֮������ĺ���̸��DZ�ʱ���Ѳ�����һ���������������ģ���Ȼ��ʱ�������Լ���ѵ�����ó�ʫ�ࡢָ��������Ů���塣��ս�������������У������Ѳ����ڳDZ���������Ϸ��С�������Ǵ����һλʥ���Ϲ����������ź��¡��������Ű�ɫ���룬����������Ĵ��ˡ���������
������������ʥĦ��˹����������ӳ�˵�ʱ������Ǩ����ʱ�����������������߽����ʵ������ս���������������˿�����150�������ǵ���Ѫ���������ڶ��ڹ�����������ģ������˱����ɶ����Ȩ�����Ρ��ɺϵ��ǣ�1918�귨��ʤ����������������Ҫ����λ��������ʿ��̴��������游����1919�꣬�ῼ�²�����������1920�ꡣ��������
��������
��һ���֡�1900��1930�긥������֮��
������������1917��7�£����ڰ�������17�����պã��ܸܵ������߲��ţ����14�ꡣ20��������״�����Ʒ���ᵽʧȥ�������ߵİ�ʹ���ܵ�ͻȻ���ˣ���û�г�ԣ��ʱ������ƽ�����˺ۣ����������һ���ӵ�ʱ�������ˡ���������
����������������ͨ��һ����ȥ���ﱤһ�Σ�̽���������ӡ���ʹ��ս���ڼ䣬����200ǧ����ĵط��dz������㣬�����Dz������͡�1917�괺�죬�������߲μ�ѧУ��֯�����У��������ɰࣨDivonne��les��Bains���ιۡ���;�������ײ����ˣ���������������ʦ��������¡�������Ⱦ�ϼ��Թؽڷ�ʪ֢��ĸ�ױ㽫������ʥĦ��˹�����������ļ�����ֻ��������һ�µܵܵIJ����ƺ��ܵ��������ǰ���ܿ�������������
����������������7�»ص��DZ�����ʱ�������ߵIJ��鼱תֱ�¡�7��10���峿4�㣬��ʿ���Ѱ�������Ϊ���������л�Ҫ��������20���Ӻ��������뿪����������������
������������1940�꣬��������������˹��Arras�����������������η��������У�����Щɥ��������������¼������չ��̣������ᵽ�ܵ����˼����20������˵�Ļ�������������ƽ��������˵�������ˣ���û��һ˿ʹ�ࡣ���������������������桢��̤��������ǹ������������Ҫ������д�����ԡ���������
�������������������������־Ӱ���Nelly��de��Vog���������Ա���Ƥ������л����Ү��Pierre��Chevrier�����飬�����ᵽ���������ߺ���Ҫ����ȥ��ĸ��������Ȼ��������ĸ��˵����Ҫȥ��һ���ط�������������ȽϿ��֣���Ϊ�����Ҽ����������ijЩ����ʵ��̫����ˣ��������ܡ�����������
���������������ŵܵ���ȥ������ѧ���˽������ˡ����ڡ���ɳ�����ܡ�����д�Ͱ�����������ʱѧ������������ľ��顣1940�꣬�����ķɻ����ܷɵ����������������������˵�ļ��仰����û�취���Ҿ��ǿ����ˣ�ʲôʱ���뿪�����������ܾ����ģ���������ľ������������ڡ�ս���ķ���Ա����д������Щ����ͻȻ����������Ȼ��������ע�⽡��״������������������������Ĵ��ڡ��͵ܵ�һ������Ҳ�������뵽�˳����£�ʵ�������ܡ���������
����������������������ƽ�������������������˾������˰����������ۡ�����ʱ�����������Ŀ־��Ѿ���ʧ��ȡ����֮���ǵȴ����ѵ����顣������ǰ���������ѣ����Ѿ�����ӭ���������������ĸ���Ը������������������
����������������������δ����ʧȥ���ˡ����ѵ���ʹ��������˽�������п��Կ�����һ�㡣�������ߵ����ݿ�������ʥͽ��������������������������ص����鴴�ˡ�����Ϊ����ĵܵ�����һ����Ƭ��Ȼ���ϴ�˼��ţ�������������������һ�š��ܵ�������������Ѱ���ܵ��ֵ���С���������
�������������ڸ��ﱤ����Ŀ���ʱ����ȫ����������֮��Ĩɱ��ȫ���˿�ʼ���İ����Ľ�����������·�ס�����ά�����֮�£���������������Ŀ��ǿˣ�Carnac���ȼ١������Ĺùð���˿��Amicie��Զ��Ӣ��������ᡤ����Sydney��Churchill����У�������ڿ��ǿ�ӵ��һ����������������������Ϣ��ʥĦ��˹�������¡���������
������������·�ס�����ά�����ǰ�����֪��������Ť�˽���ʱ����Ҳ�����չˡ����������Ӽ���������վ�������������ܼ��˵İ��ŲμӺ�����������Ϊ�ܹܵ����Ĺ�ϵ�����˲������������ả���˴���������������
��������������һ������Ӿ�ε������������������ü��˱��ܾ��š���Ȼ���˲����������Σ���������ʹ˷�����ʮ���������һ��������ͧ���δ��������ѿ����������₩�������ڼӶ��ȵأ�����ײ��ɳ��������������֮�֡���������
��������
��һ���֡�1900��1930�����ս�������
������������1917�꣬�¹���һ�δ�ս������ռ���Ϸ磬ս���ƺ�Զ��Ԥ�������ó���17�����Ѫ���꼸����������������������â���ﱤ��ͬѧ�У��ܶ����ѱ������������顣��������
����������������������Marne���뷲���ǣ�Verdun������ɱ��½����Ϊ���Ҵ����Ĺؼ������ڼ����н���½�����ӷ���������϶࣬��˰���ע��Ҫ����Ъ�常�ĽŲ������벽���š�����������飬�������뺣���Ƚ������������������֮�⣬����Ҳ�����ǿ�ı�����������Ȼ�����������̼�ͥ���ӵ��͵���âҮ�ջ�ѧУ�Ͷ����Լ�ѡ����ֵĶ��������һ�ޡ���������
���������������뺣��һ������������Ĺ��ٴ�ͳ���Ѷ���д�ļ���ʷ�У���¼���游���εİ��˹��������������β����ž��٣����ᵽ�˲μ���������ս���ľ��顣Ӣ��Ͷ��ʱ���������ڳ�����������֮һ�ǵ��Ϻ���ս�����ල�����Կ�Ӣ���ʼҺ������ж������ε������Ǻ������ٵ��������飬������λ�����Ǻ�����ξ����1778�귨����������Ӣ����ˮ��š�ʱ���ڽ��ϡ���������
������������Ϊ��������ѧԺ����ѧ���ԣ����˽�������������ʥ��Ъ������ϵ�ʥ·��Ԥ��ѧУ��ϰ��ʥ·��ѧ���ڴ�����ѧ��ѧԺ����ѧ���ԣ�һ���ֳ����顣�Ͱ���һ����������뺣��ѧԺ��ѧ������Ϊ���������ӡ�������������ʾ���dz��Ʋ����������������ľ����ѧУ����������ѧԺ�Լ�ʥ����½��ѧԺ�ȵ���������ѧ������������
������������Ү�ջ���������������в����ӵܽ���ѧԺ�ijɹ��dz���������ʥ·��Ԥ��ѧУ��������еġ��������ӡ����ǹ�������������ڼ������ᵽ���������Ѷ����������Ĺ��塣���൱ʱ��ʥ·�ײ�ϰ��ѧ��ע������30�����Ϊ�е��Ĺ�����٣�1940�꣬����Ҳ������άϣ��ʱ��������������֮����������������
������������һ�δ�ս����������ս�����ȼ�յ�Ӱ���£�ʥ·�ļ��ɻ����˼��㣬��Ϊ��ѧ���������������顣�췴�����ո�Ⱦ��ѧУ������ѧ������������ȫ���С�������ʱ��ͯ�Ĵ��������磬����ű��ڸ����ϿΡ���绰�������ӻѳ�ѧУʧ����������һ�������������踡���������ζ����ʱ�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