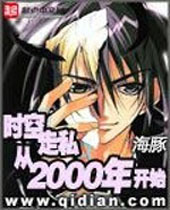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架,在篇幅不长的书中,描述了九个世纪。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讲,介绍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影响。
【建议阅读文献】
柏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The France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s School 1929—1989),江政宽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7。
《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中译本卷首,三联书店,1992。
顾良《布罗代尔与年鉴派》,载《法兰西的特性》,顾良等中译本卷首,商务印书馆,1994。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特别是此书后面所附的《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和《剑桥大学经济—社会史研讨课》书目,尤其值得参考。)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13卷3期,台北,2002。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
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这些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的空子来挑战的,它很偏颇,但也很锐利,一下子就从原来的理论的缝隙中插进来,把原来的常识搅得人仰马翻,你能不理它吗?这一讲要讲的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就是说,一个西方当代思想和方法,甚至是很特别很反叛的理论,可以怎样理解,并且运用到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的实际中来。各位要记住,我并不是主张把西方理论特别是时尚的理论全面搬来,不过,我们得承认,有的理论是可以启发思路的,特别是像福柯的理论。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他正好就是思想史教授,而另一方面,他关于监狱、精神病院、性等等的研究,恰恰又对传统思想史形成了挑战。你不了解这些挑战不行,不回应这些新的思路也不行,这些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的空子来挑战的,它很偏颇,但也很锐利,一下子就从原来的理论的缝隙中插进来,把原来的常识搅得人仰马翻,你能不理它吗?
好了,书归正传。进入正题之前,这里先介绍福柯。
1970年,经过激烈的竞争,福柯得到了一个法国最高的学术位置——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教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欧洲,得到一个教授的位子是非常之难的,比拿博士难得多,不像我们在中国,教授太多,也得来太容易。法兰西学院教授的位置,代表了法国人心目中学术成就的最高水平。1970年12月2日这一天,福柯作为新任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发表了第一次讲演。当时有一大群学者来听他的讲座,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最有名的学者,像上次课上讲到的年鉴学派主将、大家都知道的布罗代尔,那时候布罗代尔已经年龄很大;还包括写过《忧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的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我从来没看过一本人类学的著作,能写得这样引人入胜。福柯的这次讲座,后来被整理并出版,名为《话语的秩序》,这次讲演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这里回过头来简单介绍福柯。福柯是1926年出生,1984年去世。在1970年,他44岁。当年和他同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还有另外两位知名学者。一为雷蒙·阿隆(1905—1983),这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有一件事情很有名,在1955年,他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批评知识分子迷恋左倾,觉得很过瘾很有劲,其实是自欺的幻觉,因此引起一场论战,主要的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特。还有一位是乔治·杜比(1919—),就是上次提到的年鉴学派的一个著名人物,他代表着上次我们提到的后期年鉴学派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倾向,就是所谓“从地窖转回阁楼”的代表人物之一。
福柯和他们一样,在当时相当的走红。当了法兰西学院教授以后,他每年都在那里讲课,其中一个讲课记录就是现在已经出版中文本的《必须保卫社会》,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在他1984年去世后,被公认为世界上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有震撼力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这个人还是他一整套的想法,都带有一种颠覆性的震撼。大家知道,在生活上福柯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行为,在思想上他的很多说法也同样很具有颠覆性。特别是对思想史研究来说,福柯的这一套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意味。
下面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谓的“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1)
一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
在福柯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前一年,即1969年,出版了他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有翻译本,我不懂法语,不过,据精通法语的人说,看这个中文译本不如看台湾麦田出版的译本《知识的考掘》,后面这个译本,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翻译的。
《知识考古学》一书对思想史研究来说,可能产生的影响相当深。在福柯的词典里,考古学(archaeology)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简单地说,它包含着三层意思。
我们现在接受的、习惯的,所有常识性的、天经地义的、不言自明的东西,很可能都是后来才逐渐地被历史确立起来、被建设起来的,它本来不应当有免于“审查”的豁免权,但是当它成为“常识”的时代,大家都不审查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第一层,他要用“考古”的方法,重新考察我们现在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思想、信仰等被建构起来的过程。为什么说“建构”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接受的、习惯的,所有常识性的、天经地义的、不言自明的东西,很可能都是后来才逐渐地被历史确立起来、被建设起来的,它本来不应当有免于“审查”的豁免权,但是当它成为“常识”的时代,大家都不审查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觉得理所当然了。所以,福柯说,要用类似考古学的方法,来一层层挖呀,看看它的出身、来源,是不是当然合理,考察一下,它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开始逐渐地建构起来,变得合法合理的。用福柯的术语说,就是要用“系谱学”的方法,找到一层一层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考古学中一个非常基本的知识,就是对地层关系的研究。一般地说,越是下面的地层年代越是久远,上面总有一片一片的堆积层。比如我们发掘了一片文化遗存,总是明清时代的地层掩盖了唐宋时代的,而唐宋的地层又是建立在秦汉的地层之上的。而系谱学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层一层地追踪。系谱这个词,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家谱族谱。其实就是这样,你看看写的家谱、族谱,看看哪一代到哪一代,哪一代发达了,改了自己的族谱;哪一代没落了,只好归入他族。这和考古一样,系谱也是一种地层的关系。福柯运用考古学的概念及系谱关系的知识,就是为了搞清楚知识逐渐被建构的历史。
第二,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的,所以他老说“话语”和“权力”这两个词呀。他认为知识、思想和信仰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变化,是它和权力互相纠缠的结果。他认为权力能够建构知识,而知识反过来又成为权力。以前讲“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只是说真理传播还要加上艺术表达。其实更主要的是,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呀。以前有个故事讲,虽然一个人的母亲特别相信自己的儿子品德很好,但是,如果连着有三次传言,说儿子杀了人,母亲还是会跳墙逃走。但这只是谣言的力量,而有的话语,本来可能是子虚乌有,但是经过权威说出来,经过经典记载下来,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包装和宣传,它好像就是真的了,真的产生事实一样的效果了。有的话语,本来可能是子虚乌有,但是经过权威说出来,经过经典记载下来,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包装和宣传,它好像就是真的了,真的产生事实一样的效果了。反过来,权力如果没有话语,等于没有权力,因为不可能“一默如雷”,不可能只是“以心传心”,像禅宗一样“不立文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要考察“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第三,我们要问,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刚才我们说了,他的目的就是用考古学及系谱学的办法,来揭示我们现在习惯接受的知识、历史、常识、思想等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它的基础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凭什么得到这些合法性并拥有了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我们过去认为的天经地义的知识基础给揭开了、掀翻了,指出它们只不过是由权力建构的“话语”,而“话语”建构了一个知识的“秩序”。我们习惯于在这个秩序中思考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呀,于是,就形成了一整套我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可是,福柯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天”总是在变的呀,这些常识未必就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在《知识考古学》里,福柯认为,做思想史研究,应当做的是把一些原来的观念基础,从不言自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将它上面建立的问题“解放”。“解放”很重要,大家是不是还记得,第一次课里面,我已经说到,我们以前考虑问题时,思想中总会存在着一些想当然的平台,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考虑。可是,福柯对这个平台进行了颠覆性的研究,将平台自身就看成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可以把其他问题置之其上的安然稳定的基础。福柯强调,这些平台本身就问题丛生,为什么?因为它的合理性不是天生的,本来就是历史的。
我们的知识世界里面,有很多常识、有很多历史定论,过去我们并不去想它对不对,但是现在回头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怀疑的。福柯知识考古学最重要的启发,就像胡适的老话说的,就是“从不疑处有疑”呀。这是对的。我们的知识世界里面,有很多常识、有很多历史定论,过去我们并不去想它对不对,但是现在回头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怀疑的。福柯知识考古学最重要的启发,就像胡适的老话说的,就是“从不疑处有疑”呀。这里给大家举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以前,思想史里面,是不大提刘向的,最多是文献学史会提他,或者只提它的儿子刘歆。可是他负责西汉官方的校书,实际上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经典化”的工作,很多经过他校订的文献,成了经典的文献;很多本来不在一起的文献,经过他一缀合,成了一个整体的文本;很多过去重要的文献,他放在一边儿,后人就觉得不重要了。大家想想,这种对思想经典化、经典整齐化、定出秩序来的工作,思想史怎么能够忽略呢?可是以前就忽略了,也没有谁特别讨论它,于是思想史就把这一页重要的东西给撕掉了,我们也好像觉得本来就没有这么回事儿。相反,我们来看,王充、范缜、吕才三人在“道统”为中心的思想系列中并不引人注目,古代讲到“道”,那是孔子、孟子、扬雄、韩愈到二程、朱熹呀,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比如王充,常乃德在30年代写《中国思想小史》的时候,还特意讲过,你不能用他的著作来代表东汉的思想界;汤用彤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时候,也没有把范缜那么隆重地放在显赫的位置上,只有一小节。至于吕才更是不起眼,过去的大多数哲学史思想史都不怎么讲他。但是,中国学术进入20世纪后,由于逐渐受西方的影响,三人的地位开始凸显,特别是到了30年代崇尚理性和反对迷信成为我们哲学和历史的重要方法后,三人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到50年代唯物论占了主流,写中国无神论时,三人则成了东汉、六朝、隋唐历史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明星。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知识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2)
事实上,王充的《论衡》中有许多批判,就像常乃德讲的,只是反映当时神秘空气笼罩下的一般景象,不是很普遍的很重要的。直到东汉末年蔡邕还把它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