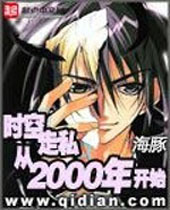5500-˼��ʷ���ý�¼-��1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ʱ���Ļ�����������ʷ�ؽ��Ͽ��ܲ��Ǻ����ã�������˼��ʷ�о���ȴ�����á����Ǿټ������ӡ���������
����������һ����α���������顷�����ʮ���֡�����ΩΣ������Ω��Ω��Ωһ���ʳ����С������DZ������Ŵ�ʥ�ʹ��ķ���Ҫ���ģ�����Ŵ�ʥ�˵�ȫ��˼�뾫�����������ˣ���Ϊ�����漰�ˡ����ġ��͡����ġ��IJ��죬�漰�ˡ������ij�Խ�ԣ��漰�˳�Խ�������ձ��Ժ�Ωһ�ԣ���ָ���ˡ��С���ԭ���ǣ�����������������δ���������˵�������м٣�����ְɡ��Դ��������賿�֤���ij����������Ժܶ��˶��������ˣ�������Ӧ���ӵ�������ķ�����ǣ�����˼����ζ�ܲ����Ͳ����������ı�������Ժ�����˼�뽫������������������й���ͳ��˼������𣿵��ǣ����ո��µ����������������Ϊ�λᱻ���Ƴ�����κ��ʱ�������ڱ�Į�ӵ��ƴ������ڴ�ӽ��ͺͲ�����δ������ڱ��ٴη��������������Կ����ܶ�˼���Ǩ���������ﱻȨ����װ���������߱�Ȩ������һ�߶�����ʷ����������
���������ڶ����ǡ���������ۡ�������������ۡ�Ӱ���й�����ѽ������˵�����й���̵ĸ����ء���������ӡ��ԭװԭ�������Դ��ձ��˽ҷ������ij����������Ժ����˴����ۣ����ǿ��Կ����ڹ�ȥ�����ڡ����顷�ϵ�һƪ���¡�����α���Ƿ�֮�䡷�����˾Ͳ�ͬ���ձ��˵�˵����˵�ⲻ�Ǽٵģ������ӡ�Ȼ����������й��������Ͼ�֧����ѧԺ���人�й���ѧԺ��̫���������Ҳ������������ΪʲôҪ���ۣ���Ϊ���մ�ͳ����ʷ����������ɾ��䴫��ģ������Ƿ��ӵĻ��Ȩ�����������ž��Եļ�ֵ��˵���棬��ô���ͽ����������â���ɣ�˵���٣����ͳ��˲���������Ĺ�ʺ�ѣ�ֻ�ܽ���ʩ�ʡ�������α�ı��������������ı��������ұ��۵ķ���������ȥҲ�Ǻܿ�ѧ�ģ�Ŀ¼��û�У���������˼��Բ��ԡ����ǣ������кܶ���������ľ��ǶԵ��𣿼ٵľ��Ǵ�����˼�����Եģ���һ��˵�����ǡ��桱����˼�벻���Ϸ�̵�ԭ���ѵ���һ���ǡ��١��𣿺�����������Ҳ�����ˣ�����һ��˵���Ƚϸ�������˵����ѽ����˵���Ǽٵģ���ô���Ǽٵİɣ����Ǽٵ�Ҳ�ã�˵����ô������˼�룬ԭ�����й��˵�˼���ء����������������ǡ���������ۡ�����������һ������������Ҫ�ǰ���֪ʶ����ѧ��˼·��ȥ�����ÿ������¼������⣬���������й��˵���Ʒ�����Ҵ�����������α���������Ƿ������������˼�뱳�����������õ���Ȼ���ձ��˵Ŀ�֤��ȴ�ѽ��۵���һ�����������Ǹ�ʱ�������������ַ�������������Ƿ�����Լ���ʱ��˼��ת���йأ���ʵ������ѡ���������ۡ��ڽ�����������Ϊһ��˼��ʷ�¼���һ��һ��ؿ��죬���Է����ִ�˼�롢�ִ����˼��ĺܶ���Ȥ����������Ǹ��������ϵ�˼��ʷ�о�����������
�������������������������᷻α�졶ʫ���Ĺű��͡���ѧ���ű�����ȥ���ڷ᷻���Ǻ��Ʋ���ģ�˼��ʷ����ѧʷ����û������Ӱ�ӣ�����һЩЦ����������һЩ����Ц������ҿ���ȥ�������ˡ�����خ����Ϊʲô����Ϊ����٣��졶ʫ�����ű������˹�����˵������ʯ��������ѧ����˵������ŵı��ӡ����Ǹ�ʱ������ŵľ�����õġ�Ϊʲô���ӽ�ʥ������Ǵ���һ���濴ȥ�����Dz�Ҫֻ�����ٲ��٣�Ҫ���������ֵ��Ǹ�ʱ��������Ϊʲô��Ҫ��٣�������1922��8��23�յ��ռ������˵����Ҧ�ʺ㡶ʫ��ͨ�ۡ������ġ�ƣ��q��һʫ�Ľ����м䣬�����������������Ʒ����ξ�ʫ����ˣ���Ϊ�������ѷ������ʲ��ܲ������ӹ���������������������ñ�ӡ������ǶԵģ�α��Ķ�����������˼��ѽ�����̨꣬��������ɭ���ڡ��������ڵ���α��˼�����ۡ���˵������������������ѧ�ɺ�ά�����ӵ�ѧ��֮�䣬���۲��ݣ��������йű�����ѧ�����Ʒ�����ѡ���ѧ����Ϊ�������±���Ȩ���ԣ�����һ����˵������ű�û�и��ݡ������۲��ݵ����ʱ�᷻������ʯ���������˸������ã�ʲô���ã����Ǵ�����߶�����˵�᷻ƽ����������������������Զ�孵����ܣ����Ǽٵ�ѧ�����ں��У�������һ�������������Ǽٵ�ѧ����ѧ��������ֺ������йء�������ҲҪ���ô�ͳ���Ź���������������ѵ�ʱ���߶�����һ�¡�����ɭ����ƪ���µľ��ʴ������dz�Խ�˼�������α��֤�������������֪ʶ��ϵ���������ص�˼��ʷ���⡣��������
�����������ĸ����ӣ��ǹ����δ���ʷ�ġ���Ҷ�֪����������Ӱ���Ĺ��£�˵������̫�����̫�ڵ����顣����Ө������ɽҰ¼��˵����̫���Կ�ط��һ����ʿ�Ļ�˵�����ʮ�¶�ʮ��ҹ�����죬��ͻ����Ի�ܳ���������ǣ������Ҫ���ˣ�Ҫ�Ͽ촦�����¡���һ��ҹ���Ȼ�������𣬶�����ѩ�±������ǣ��������ĵܵ��Կ���Ҳ���Ǻ�������̫������һ��Ⱦƣ��������˶��뿪����ʱ����ԶԶ�ؿ�����Ӱ�£��Կ��塰ʱ���ϯ���в���ʤ֮״���������������죬ѩ�Ѿ��ܺ��ˣ�����̫�����˸��Ӵ�ѩ��˵�����䡰���������������Ǻ��Կ���һ���ڴ���������˯�¡���ʼ������죬�����������û���������Ѿ�ȥ���ˡ�������£������˺ܶ����ۣ������Ƿ���̫�ں���̫�棬�ܵ�ɱ�˸�磿�ر��ǣ�ͬʱ����һ�ִ�˵����̫��Ϊ�̳��ˣ�ԭ���Ƕ�̫�����˼������̫�����˼���ɼ�������Ȩ��֮����������һ�ִ�˵����̫���Լ�����˼������˵�����δ����գ����ǵ�ʱ����Ӱ�졢����Ȩ�����Ǹ���������̫��Ķ���Ϊ�ʵۣ�������̫��ĵܵܣ�����̫�治ͬ�⣬��������д��گ�顣���Ժ���̫�ڶ����պܲ�ϲ����
��˼��ʷ���ý�¼�������µ��������й�˼��ʷ�о�֪ʶ����ѧ��Ұ�е�˼��ʷ���ϣ�2��
��������������һ��˵��������ʾ�˱��γ���Ȩ�������м��һЩ��Ӱ�����ǣ���Ϊ��������������д��������ͨ�����ࡷ��Ҳ��¼��������£�����û�а���Ө��˵����֤��������ԣ����¶��ͳ����ɰ����������ų����걸Ҫ��������ʷȫ�ġ�������ʷ���±�ĩ���ȵȶ���������ι��¡����������Ν�Ɯá��������ȵȣ�����Ϊ��̫��˵����˵����û������¡����������������������κ��飬�����������ֹ��£�˵�ܿ�ϧ��̫�ڣ���Ϊ��������Ȼ�������˲��𣬿�����������۵㣬��������Ң˴��ҵ������˵����Ӱҡ�죬�����ڡ�����������
��������������û��������飿���������˲��š����չ�ȥ����ʷѧ��ͳ����Ҫ��Ҫ��֤��������Ļ��Ǽٵģ�����Ԫ�˵��������棬�硶����ǰ¼����������������Լ�����´��������Ԫ����Ԭ���������ɽ�ʷ�ѷ�����״����һֱ�ڱ��ۡ����˴Ӽ��ص�ì���п�֤������Ϊ��֤������α�������ص������αҲһ�����ɣ����˴���̫�ڵĵ����Ͽ�֤��һֱ���ִ��������ۡ��ҵ�ѧ��Ƥ��������ʮ��ƪר�ű�������������ģ��ӵ˹����������ҵĴ�ѧͬѧ���������е�˵����ģ��е�˵������ġ����˻��Ӳ�����˵��̫�汩���ǿ��ܵģ�����̫��ıɱ��������˵������̫���Ƿ�ɱ������磬���ûʵ�λ�Dz��Ϸ��ģ���Ϊ����ɫ��������Ȥ�úܡ���������
����������ʵ�����¿�����ԶҲ�����壬��ʷ���ϲ����ˡ�����������һ����ȥ���룬����һ����Ϊ������Ȩ�����ɱ������ܶ࣬��̫�ڵ�ǰ�棬�ܹ���ܡ��̣���ا�Բ�ֲ�����������ɺ���Ԫ������������������馶Խ��ĵۣ����������ģ����ܡ��ֵ�����ǽ�����ڴ���ս���Ѿ������������ˣ�����Ȩ�����ջ��ǿ�ң��ʵ۵�λ�Ӻ������ˣ�����Ҫɱ��ɱȥ������ΪʲôҪ���Σ����һ�Ҫ����Ϳ�������������أ���ô�������ԭ���Ƿ���Կ�������ͳ������ʷ����͡��Ϸ��ԡ�����Ҫ�����Ѿ��������˶ԡ���Ȩ����һ����Լ��ͬ������֮����Ҫ���ڣ��Dz�����Ϊ����������ֽ����ڸ�������ѪԵ�����ϵ�������������ս�أ��ر��DZ��������������Ӱ�������飬ΪʲôҪ˵�����桱���ǡ��١��أ�˵�����١������ɾ�������ʷ��ʵ��֤�ϵģ����dz��ڡ�Ϊ���䡱��Ŀ�ġ�����ȷ�������Ϸ��Ե�Ŀ�ġ�����������������أ����ԣ���֪ʶ����ѧ��˼·���룬�����Dz��ǿ��Կ���һ����һ��˵��˼��ϵ�ף���һ��Ϊʲô���֡���λ���ġ������͡����������ᱻ������ô���أ���ʵ�����е����µ��ˣ�����������ı���ñ���������̫�治Ҳ���۸��¶���ĸ��������ۼ������˻ʵ��𣿵ڶ���Ϊʲô��̫�ڵĸ�����Ӱ������Ҫ��Ī�����أ�������Ϊʲô����һ��Ҫ��֤������������ǡ�����٣������ѵ������á�֪ʶ���š��ķ���������������鱻������ͼ٣������۳��ǺͷǵIJ�ͬ������Ϊʲô�������ȥ����������
��������˳��˵һ�����ӣ�������ֵ��Ϻ������ս������ݳ��ϡ����С�������ȡ��һ�䣬��仰����Ҫ�����͡�ս���ߡ���ߡ�����ġ�����֧������������¡����������ӡ��ⴢ˵������������������λ���棬��֮����������������ࡣ���ɽ������ָ������˵���������еĹŴ���˵�������λ��ɱ֮����˵��������ֻ��һ��˵�����ڹŴ�����һ��˵�������ܣ����ñ����Ǵ�ҹ�ʶ�еġ��Ϸ������ģ���֮��Ӧ�����棬�ǵ�Ȼ�����飬���ǣ���ȴ�ɴ�ɱ���棬��λ�ӵ����Լҵģ��Ȿ�����Ϸ������ǣ��������ܸ����ഫ���˹��������Ծ�˵�����ǡ������λ����Ȼ��˵�ǡ���ɱ֮������֤����Ϊ��һЩ�����Ĺ������֣��Ŵ�һЩ���������Ĺ��£��ͳ�������ʷ�����о�д�ˣ�����ȥ�ˣ���ô������Ϊʲô����������
������������㡵����ԡ�αʷ����������ʷ���������븣��˼����Щ��Լ��ͬ��һ�£���ʵ�������кܴ�IJ�ͬ������������ʷѧ�ң���Ҫ��취��αʷ�Ϸ��ں��ʵĵط�����ʷ���ã���Ҫ�����Ϊ�桱�������Ϊ��������������˼��ʷ�ң�������˵����д��ʷ������˼�룬��α��������Ҳ��˼�롣����㡵����ԡ�αʷ����������ʷ���������븣��˼����Щ��Լ��ͬ��һ�£���ʵ�������кܴ�IJ�ͬ������������ʷѧ�ң���Ҫ��취��αʷ�Ϸ��ں��ʵĵط�����ʷ���ã���Ҫ�����Ϊ�桱�������Ϊ��������������˼��ʷ�ң�������˵����д��ʷ������˼�룬��α��������Ҳ��˼�룬����һ������α֮��û�м�ֵ��𣬡�������ʱ����١�������֪ʶϵ���е�һ�㡣���仰˵����ʷѧ�Ұ�αʷ��������һ��ʷ�Ͽ�����ֻ��Ҫ���������ģ���˼��ʷ�ҿ��������α��ԭ���ذ���������ģ���Ϊ������ͬ���е�ʱ������������˼������ʱ���Ƕ���α�Ķ����Ľ��ܣ�Ҳ��˼���������ã���Щ�����Ǻ��˵�ʱ�Ĺ�������������ͱ������ˡ�ͨ�����������š���ѧ���롰���ԡ��������Դ��δ��������֮ѧ��������ʶ����Щ�����Ǽٵģ��ͳ��������ǡ�ȥα���桱������Щ��������������ʷ�桱���ɹŷ������������ġ���ǰ�о�����˼��ʷ�����ǾͱȽ϶���ں���ʲô���ף�����˵��ʲô����Ϊ�ܶ����Ͽ����м٣����ԣ��㲻��������˵�����������õ����Ͼͺ��٣�����Ҫ�ȱ�α��Ȼ���ٰ���ļ����������Ÿ���Ȼ��д��ʷ�����ǣ�����ȴ��һ���������ã����������α�Ĺ��̱�������һ����ʷ����һ��ѧ��ʷ��˼��ʷ��ij��������˵����������Ҫ�����ǰ�ϰ�ߵ���������룬��Ҫ����IJ���������˵Щʲô��˵�������Ǽ٣�����������ô˵���ں�ʱ˵�Լ�ΪʲôҪ����˵����������
������������һ����Ҳ���Ѿ���˵�����Ķ������ͱ�ò���Ҫ�ˡ������¿���������ص��ĵز��ϵ�У����·�������һ��������仯����ʷ������Ϊ���Ǹ����ࡢ����������ʷ��������������ݽ�����ʷ������������ϣ����µ߸��˹�ȥ��ͳ�ķ������������ķ����£���ȥ������Ϊ����α��ʷ�Ͼͻ�dz����á���ǰ˵�����ڷ���кܶ��α�����ɾ����Ǽٵģ��о����ʷʱӦ���ȿ�֤�����Ȼ�����ų��������ձ�һλ������ѧ�����������Է�̵���α��������ϸ�µ��о������Ĺ�����α������������Ϊ�Ƿ��ʷ�о������������ǣ���ֻ�ǿ�֤�ⲿ������ģ��Dz����Ǽٵģ������IJ������ɣ�������ע�⣬Ҫ����ģ���Ҫ�üٵģ��Կ��ɵ�ҪС��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