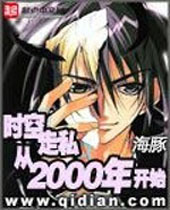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从历史时间角度看,它提供了重建古史系统的基础。
随着现代的科学主义和中国传统公羊学的结合,古史辨派产生了,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疑古呀。这种疑古的风气,对传统古代史产生了冲击和破坏,瓦解了过去由各种传说、神话包裹起来的古史,同时,又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思潮遥相呼应。白鸟库吉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尧舜禹抹杀论,认为尧舜禹都是神话,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上古史,在1909年的《东洋时报》131号上发表的《中国古代传说之研究》里面,白鸟说,第一,尧舜禹是儒家的传说,三皇五帝是《易》和老庄一系的传说,后者是以阴阳五行为根据的;第二,尧舜禹这种儒家的说法,表现上层社会思想,而三皇五帝表现的是民众中的道教的崇拜;第三,道教其实是道家,是反对儒家后才整顿成形的,所以三皇五帝发生在儒家的尧舜禹之后;第四,尧舜禹是根据天地人三才说推衍出来的,所以尧舜禹不是一个时间上先后相继的历史,而是一个并立出现的故事。
顾颉刚他们是不是受到白鸟的影响?不很清楚。也许受到过,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白鸟库吉的目的,是瓦解中国古史在亚洲的地位,解除古代中国历史对日本文化的笼罩。然而,顾颉刚与胡适古史辨的思想,更主要的,是愿意接受一些可以称得上“科学”的论断,就是我们以前曾提到过的“有罪推定”的思考模式:先预设没有得到证明的古史都是假的,把传统正史资料中所编造出来的故事统统扫干净。抹满色彩的一张纸上无法重新书写内容,于是他把所有的色彩一扫而空,所以他说因为“疑古”,所以西周的历史没法写了。
可是,这是一个清道夫式的工作,破是破了,没有立呀。古史的时间和空间,过去是由传说构成的顺序,给我们建立一个线索,但是这个线索没有了以后呢?我们靠什么重新建立古史的脉络?这个时候,甲骨文的发现,给重建古史提供了基础,使古代不再是一片空白。特别是,当王国维用甲骨文证明《史记》中殷商早期先公先王系统的正确性,甲骨文就提供了重建古史的系谱基础。所以说,王国维的这份功劳是很大的,这篇《先公先王考》的学术意义是很大的。其实他不止是考证,他还有很大的关于“文化”的判断,我在日本发现了王国维寄给内藤湖南的手稿,在考证后面就有一篇《余论》,这是大议论呀,只是这些意思后来写在《殷周制度论》里面去了,所以在后来出版的《观堂集林》里面就删去了。可是大家都不注意,以为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证,其实不是的。应该说,顾颉刚等人把原来的传说扫清了,王国维以后,就用甲骨文资料,在这张白纸上重新写一份古史的系谱。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中国古代史才能越来越清楚。第二,从地理和文明的空间角度看,这些考古发现把思考中国历史的空间背景扩大到了汉族文化圈之外。
新的考古发现,还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与周边历史关系的兴趣。比如,敦煌文书的发现,刺激了当时人们对中西交通史的兴趣。我们知道,晚清时有一段时间对西北地理很关心,比如徐松、沈曾植、张穆这些人,但那时的关心,一是站在清帝国的立场上,注意到西边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与中国的相互关联;二是对元史的兴趣,他们很少有非常确凿的资料,而且沈曾植、徐松、张穆等人都不具备多种外文的阅读能力,更不用说去实地考察。敦煌文书发现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敦煌、吐鲁番是在中外交通的要道上,那里保存下来的文书,不仅仅有汉语,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语言,如梵文、吐火罗文、突厥文等。这样,中国历史从而就进入了世界背景中,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对其他语言,甚至是一些死去的语言的研究能力,这样才能进入世界学术界的对话里面。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敦煌文书出现后,佛教与道教的争论也渐渐有了新的研究,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变化也成了重新被关注的焦点。所以,在空间上,使中国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些问题:研究汉代就要注意到贵霜王朝的丘就却、阿育王这些并非中国本土的人物,这样才能搞清佛教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佛教大多是从印度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的,可能在那边有一个佛教兴起和衰落的过程,那里的势力消长,会像波浪一样影响到中国。所以研究中国佛教,不能仅仅守在汉译佛经之中,必须去了解印度。而研究唐代呢?又必须了解吐蕃、南诏,包括古代的大秦、大食、天竺和中原的关系,你不能只管汉族地区这一块儿了呀。此外,居延汉简的发现,同样也刺激人们去知道中国的边缘地带是什么样子,不能只关心汉族的中心地带。第三,这些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资料,让人们考证过去所不知的东西的起源。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2)
这方面的例子呢,比如戏曲和词的起源,大家都知道,是要靠敦煌文书来研究的。在敦煌资料发现之前,我们只知道《花间集》、《尊前集》,认为这是最早的集子,可这实际已经是五代的、已经是文人的很成熟的作品了。可是敦煌发现的文书里面,有《云谣集杂曲子》,写在我们现存的词曲之前,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考证这一类歌曲的最初形态的资料。又比如,有人靠敦煌发现的变文、俗讲研究小说的起源,靠敦煌发现的舞谱,研究古代音乐的情况。像大家熟悉的季羡林先生,就用西域发现的吐火罗文本的《弥勒会见记》残片,考证古代戏剧的起源,这些都使我们在传世文献之外,有了更多的没有被改造过的资料。
第四,引起学术研究方法尤其是文史研究方法的深刻变化。
甲骨文、敦煌文书、汉简和大内档案都不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资料,这使学术研究者被迫要接受和了解新资料,于是学术研究方法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注意考古发现和文献的互相对证,其次,是域外资料与域内资料的对证,再次,就是使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过去,尤其是沿袭了清代学术传统,我们习惯了使用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通鉴》、《史通》等传世文献,但甲骨文、敦煌文书、汉简和大内档案都不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资料,这使学术研究者被迫要接受和了解新资料,于是学术研究方法开始发生变化。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总结学术史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一点,依我的体会,他讲王国维,实际上是在讲王国维所造成的整个学术史的变化,这个主要变化是:首先,注意考古发现和文献的互相对证,这就是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其次,是域外资料与域内资料的对证,这就是陈寅恪讲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不仅知道中国的资料,还要了解外国的资料,如研究蒙古史就要知道外蒙古史,研究吐火罗文还要到德国去留学,还要读一点佛经,懂一点吠陀。再次,这是陈寅恪没有提到的,就是使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如大内档案非常琐细,有审判、官府报告、每年或每月例行地向中央报告一个地方的情况等,这些常与民间文化的研究相联系,民间文化研究很强调以实地调查为主,像捻军、义和团、地方宗族的历史研究,就离不开田野调查资料,而佛教道教史,就更需要田野的调查。我近来看到法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关于现代民间斋醮仪式的一些调查,对民间道士收藏的仪轨抄本的收集,就对古道教史研究有很大帮助。于是,这三方面就成了我们后来研究历史必须注意的一些东西,即考古与文献、域外和域内、调查和历史研究。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学术有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历史学的变化,和这些考古新发现是有关系的。
第五,学术研究的手段和技术的变化,不同的学科开始互相关联。
当西方的考古学被运用到中国的发掘上,这时,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就开始进入中国历史研究。大家要知道,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很多来自于地质和生物学,分析地层关系时常用的是生物学中孢子的知识,地质学和生物学的背后一整套的支撑是进化论,非常清楚的系统进化理论,这些随着地质学生物学进入考古,也就进入历史研究。看考古学方面的论文,我们会发现他们好像有另外一套规矩,比如考古中讲的某某文化,“文化”一词与我们所讲的“文化”是两回事。当这些知识进入考古,考古的知识进入历史,那么,历史背后支持的知识就发生了变化。同时,因为考古的新发现,地理学和语言学也开始在历史学中越来越重要。历史和地理是分不开的,这不仅指传统中国的历史地理的地名行政沿革,还包括生态等很多学问,语言学的知识也变得很重要,有一个清楚的实例是,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当时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把历史与语言放在一起。因为很多新的有别于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常常是与语言学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以外,还有如同位素放射、纸张和抄写字体的辨认等也是新的技术,过去只有在辨别宋元明清版本的时候才有对纸张的辨别,后来,这种辨别技术远远超过了当时。
总而言之,考古发现对学术史的影响始终是很深的。这就好像死海文书与圣经学的关系一样。死海文书的发现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震撼性的事情,尽管现在死海文书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因为西方人很多的知识、思想、观念与《圣经》都有关系,《圣经》是他们的文化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当库兰的死海文书被发现,许多观念就真的受到冲击,很多历史要重新书写。同样,当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汉简、大内档案在上个世纪初到20年代逐渐被发现和整理以后,中国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才算是进入了现代。
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考古发现对学术史的影响,但7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现的意义,是绝不亚于以上这些考古发现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讲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1)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常常有一个“时间差”,当考古刚刚发现东西时,人们不一定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意义,总要等一二十年过去,它的作用和影响才开始慢慢发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常常有一个“时间差”,当考古刚刚发现东西时,人们不一定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意义,总要等一二十年过去,它的作用和影响才开始慢慢发挥。
比如甲骨卜辞是1899或1900年发现的,真正把它用在历史研究中,并深刻改变了历史研究方法是在第二个十年,也就是1910至1920年。这时,王国维、罗振玉开始逐渐写出一些东西,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敦煌文书呢,也是1900年藏经洞被打开后发现的。但是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研究路向,我觉得,实际要等到1920年代末,胡适用神会的资料来研究禅宗史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敦煌卷子对传世文献的冲击。而异族死文字书写的文献用于中国古代研究,又是更晚一些,到陈寅恪才真正有实际成果,那已经是1930年代初了。至于说大内档案,被很好地利用在历史研究上,也要隔十年以上的时间。所以,现在历史研究中被用的比较充分的考古资料,大多是70年代的发现。当然,最近因为考古很红火,洋人也很注意,所以,这种时间差越来越小了,像郭店的东西,学术研究的跟进就很快很快。
从1971年开始,第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马王堆帛书。70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先后发现几座汉墓,里面出土了《周易》(包括经和传)、《老子》等等,此外,还有黄帝书(包括十大经、称、道原、经法等)附在帛书《老子》乙本后面,是过去所没有见过的。出土的《老子》与传统本子不同的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帛书《五行》篇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荀子曾批评子思和孟子“倡为五行”,“五行”究竟为何物?从帛书《五行》,可以看出在思孟时代“五行”是比附于仁义礼知圣,是内在的道德,而不是阴阳五行。还有《刑德》用阴阳数术解释四季,“刑”象征天杀,“德”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