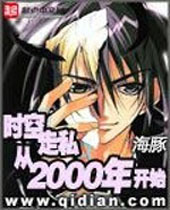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实上,在文史研究中,有许多不加讨论的,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是有许多问题的。刚才我们讲,在90年代以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一种共同的思想、感情、观念支持下,似乎根本不需要想这个“基础”是否合适,是否正确,大家觉得这是“常识”。可是,90年代后,这种同一性已经被瓦解了,所以大家都得去不断反省常识,可是,平常我们对常识总是“日用而不知”,不觉得它的存在,就好像空气无处不在,却最容易被忽略一样。打一个比方说,凭什么你会相信飞机那几十吨重的金属东西能在天上飞而不把你摔下来?你要讲清楚这点,需要懂得空气动力学,需要懂得各种各样学问,但我们大家都不必具有这种疑问,就是相信它可以飞起来,是安全的。于是在这点上,空气动力学之类的知识就是“常识”,谁也不去怀疑飞机会飞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讨论怎么坐飞机,坐哪一趟飞机。再比如说,很多人都有信用卡,可是,我要问你,你凭什么相信那张信用卡能把你的财富都搁在里面?那不过是一张卡嘛,就好像我们大家现在兜里揣的钞票就是纸嘛,你为什么相信那张纸呢?可是谁也不问,也觉得这是“常识”,要是倒退回去一两千年,鬼才会相信这些硬片片或纸片片呢。一样的呀,关于古代中国文史,很多知识也是有预设和前提的,而这些预设和前提,就是一些讨论的基础,过去,这些基础是不需要讨论的。
我们在历史研究的方面举三个小小的例子。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特别是李学勤先生,在1992年前后,在我们一些朋友的小型聚会上,他讲了这个题目。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这个要走出的“疑古时代”是针对顾颉刚讲的。第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特别是李学勤先生,在1992年前后,在我们一些朋友的小型聚会上,他讲了这个题目。后来由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整理出来,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辑上面,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这个要走出的“疑古时代”是针对顾颉刚讲的。过去顾颉刚的《古史辨》,怀疑古代的很多文献的可靠性,它的预设是什么呢?就是凡未经证明的历史文献,可能都有问题。但是,现在来看,这种前提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好像法律上的“有罪推定”,先预设这些文献都不可靠,然后再一一甄别平反。可是,如果一时半会儿你找不到证人怎么办?你就只有坐班房下大牢,这些文献就被判定成“伪”。以前张心徵的《伪书通考》就把一大批书都算成了伪书。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种“无证就伪”的有罪推定,就是我们对于历史文献的“常识”。大家看看张心徵编的《伪书通考》就知道了。可是,现在考古出土的资料证明,这里面冤假错案很多。可是,尽管是这样,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是不是换个方式就行了?既然“有罪推定”不行,那么咱们来“无罪推定”,凡不能证明它是假的,都算成是真的。如果这样一来,一大批可能有问题的家伙就纷纷逃出大牢,无数文献就都进入了历史,可能也有问题。以前历史学家他们千辛万苦重新考证的历史文献,就要重新翻案,这可能也不对。就像美国那个著名的运动员兼演艺明星辛普森,大家觉得他明明杀了人,可是就是因为“无罪推定”的前提,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就能让他逃脱惩罚。现在,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基础,就产生了种种问题,究竟考据应当有什么样的基础?这显然还是很麻烦的事情。另外,我在文学研究方面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真还是假?如果它是晚唐司空图的,那么文学批评史和古典美学史就可以在9至10世纪写上一笔,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可是,我的一个朋友,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很善于做文献考证的学者,就说它是假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一直到元代、明代,也没有人引用过它,按照“有罪推定”,那它可能就是作假的。但是,也有人反驳,按照“无罪推定”,你拿不出证据证明它是元人、明人伪造,那它就是真的。这成了一大公案,你看,是不是讨论和考证的预设、前提、基础很重要?
第二个,最近有人再次提出元稹笔下的崔莺莺,可能是“酒家胡”。这个话题是从陈寅恪那里来的,不过他给陈先生的推测上面再加上推测,也没有更多新证据,这给报纸一宣传,就变成了一个大发现,说发现崔莺莺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这个教授本来不是这个意思,怪不得他;但是,他也没有考虑陈先生当时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其实,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里面,关于这一问题是一种大胆想像,并没有小心求证。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陈寅恪提出莺莺虽然不是本人真名,但莺莺本人的名字一定是复字;第二,唐代复字为名的女子很多,比如“九九”,元稹诗里也有代九九;第三,“九九”二字古音和莺鸟鸣声相近,到这里,陈寅恪没有往下说,只是说,可能元稹会用这种名字来指他的情人,“惜未得确证,姑妄言之”;第四,在《附校补记》里面,又进一步推测,元稹诗里面有《曹十九舞绿钿》,是否“十九”会是“九九”之讹?第五,《北梦琐言》里面说到“大中至咸通年间”很多中书都是蕃人,其中有姓毕、白、曹、罗的,曹九九“殆出中亚种族”;第六,中亚人善于酿酒,故事发生的蒲州,唐代以前就是中亚胡人的聚集地,所以,可能崔莺莺就是“酒家胡”。大家看,从崔莺莺真有其人,到可能是“九九”,到“曹十九”可能是“曹九九”,姓曹的可能是胡人,到可能善于酿酒,因而是“酒家胡”,这里有多少猜测。可是,大家一定要记住,陈寅恪已经两次申明,他是“姑妄言之,读者傥亦姑妄听之”,所以我们不能指责这种猜测。但是,如果现在的学者要凿实这种推测,他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推测背后的“前提”或者说陈寅恪的“预设”呢?没有。为什么陈先生会做这样的推测?大家看陈寅恪的研究,很多都有一个倾向,就是中国文化史上,尤其是六朝隋唐,有很多东西是外面来的,比如《四声三问》讲汉语四声的分辨来自梵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李唐皇室母系是胡种,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和陈寅恪的学科背景有关系,他对中国周边的民族、历史,对中外关系史,对来自异文明的文献比较熟悉,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常常会不自觉地往这方面想,另一方面可能和陈寅恪的文化观念有关系,其实在文化上,他是世界主义者,所以并不忌讳说好东西来自外国异族。同时他又是民族主义者,所以强调要恪守民族文化本位,这种观念会影响甚至支配他的考证和判断。记得胡适和汤用彤谈话,胡适说他最不愿意说一切坏东西都是外面来的,汤用彤说他最不愿意说一切好东西都是外面来的。这两种学者的预设或前提,如果用到历史考证上面,会有什么结果呢?记得胡适和汤用彤谈话,胡适说他最不愿意说一切坏东西都是外面来的,汤用彤说他最不愿意说一切好东西都是外面来的。这两种学者的预设或前提,如果用到历史考证上面,会有什么结果呢?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思想史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总觉得过去的思想史都过多地集中在精英和经典上面,从老子、孔子一路下来,可能有一些基础的判断。首先,是大家都认定,思想都是自上而下的,鲁迅当年就说,民众是以士大夫的思想为思想。其次,这些士大夫的思想都在经典文献里面,有文字资料可以研究。再次,这些思想真的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中起着绝对的指导和支配的作用。所以当然思想史就应当写这些东西,你研究思想史,不必考虑,就是这么写就行了。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基础观念提出疑问:第一,经典里面真的是精英的全部思想吗?思想真的和制度一致吗?制度真的能够贯彻到生活世界里面起支配作用吗?社会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常识真的和这些精英和经典完全重合吗?恐怕不见得。第二,士大夫的思想和观念,不也是从一般教育中奠定基础的吗?他们一开始不也在乡村家族社会生活,在普通的私塾、书院里面读书吗?为什么一般社会生活和政治经验中的常识和观念,就不会对他们发生影响呢?他们的思想不也是为了回应这种普通的一般的社会生活吗?不成为制度、习惯、常识的思想能够影响和支配社会吗?第三,思想只在文献中间存在吗?难道其他的历史遗存中间没有思想的痕迹吗?如果你这样追问下去,原来思想史的“常识”就要动摇了,思想史可能需要重新写了。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基础的动摇与瓦解
三基础的动摇与瓦解:以国家、传统、现代为例
这当然还只是具体的历史研究和文献考证上的例子。其实,近来在研究文学、历史的根本观念上,更有很多我们平常不去考虑的基础和前提,发生了动摇甚至瓦解。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化的研究中的这许多基础,过去我们并不怀疑,比如:首先,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估价和感觉,大家过去会强调它的连续性、内在超越的追求,可是现在不太对头了;其次,对于古代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比如强调礼乐制度和习惯的特点,“五四”前后对这一特点的批判和评价,大多是负面的,现在呢?也不同了。再次,对于民族国家的确定性和正当性,也有问题了,比如,研究历史以“中国”作为当然的空间,可是现在也有问题了;第四,比如向着现代化方向的历史路向,五个社会阶段论也好,中国与西方的冲击—回应也好、新民主主义论也好,可是现在都有人质疑,如此等等,现在许多东西都有了疑问,这些疑问不仅很多,而且很严厉。
我们过去常常不假思索地说“中国”这个词,可是,你要小心,怎么理解先秦时代除了中原之外的各个蛮、夷、戎、狄的存在?在宋代你怎么评价和同样是“中国人”的金元打得不可开交的岳飞和文天祥?我们以“国家”、“传统”和“现代”为例。
——如“国家”。我们过去是认为天经地义的认同对象,但是“国家”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天经地义的吗?比如“中国”,它是否和中华民族、中国文化能这么重叠,好像是民族和文化的代名词吗?国家的统一性,常常是在文化的多元性中,被历史种种因素建构起来的,它有时会强制性地把多元的文化压扁呀,你看,像前南斯拉夫中的阿族、塞族、克族、东正教徒、穆斯林被混在一起,那么“南斯拉夫”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那种不加分别的“爱国”是否就天经地义合理?所以,现在开始就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样的思想家,说国家只是被语言建构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他曾经说,那种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其实常常只是被后来的爱国歌曲、政治宣传、历史传说等等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思想家,说国家只是被语言建构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他曾经说,那种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其实常常只是被后来的爱国歌曲、政治宣传、历史传说等等建构起来的。他问,那些互不相识的人,怎么能够互相认同为一个民族国家?那么,中国呢?所谓炎黄子孙呢?台湾有一个沈松侨,就讨论到所谓“黄帝子孙”的说法。他说,其实黄帝的传说盛行,和晚清民国初年的民族国家认同有很大关系,并不是大家原先就共同认同是黄帝子孙,而是在那个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象征,才在那时极力塑造一个共同先祖,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也好、延安边区也好,都会祭祀它,以它作为民族动员的象征力量。所以,我们过去常常不假思索地说“中国”这个词,可是,你要小心,怎么理解先秦时代除了中原之外的各个蛮、夷、戎、狄的存在?在宋代你怎么评价和同样是“中国人”的金元打得不可开交的岳飞和文天祥?你看石介写《中国论》,那个时候有中国的空间、民族、敌我观念了,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论“中国”,而以前不需要讨论呢?或者说,石介心里面的“中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吗?
——又比如“传统”。过去我们习惯了把它和“历史”连在一起,使它看上去好像真的是一点一点由古代而来的,是沿着时间这个线索一层一层积累起来的,有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