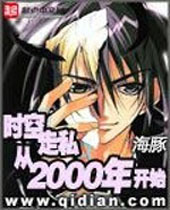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比如“传统”。过去我们习惯了把它和“历史”连在一起,使它看上去好像真的是一点一点由古代而来的,是沿着时间这个线索一层一层积累起来的,有实在内容的东西。所以李泽厚提出“积淀说”,大家都觉得很对,传统就好像背后长长的影子,抛不开,扯不散,如影随形。但是,现在的一种说法说,它并不是一个“历史”,而是一个“现实”,它只是被后来的人的语言、愿望、观念加上现实的需要,在历史中间寻找资源,一点一点建构起来的东西。像王充的思想,在东汉后期蔡邕的那里,还是“秘籍”呢,后来在种种解释下面,才成了“汉代思想传统”,进了思想史;像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它就是在晚清重新发掘历史的时候,被发掘出来的“新传统”,因为黄的书很长时间没有人读,怎么积淀成为传统?而他的民主思想也是在现代西方民主思想的解释,比如孟德斯鸠的比照中间,才被认识意义的嘛。所以在现在,“传统”有时不再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实在性和历史性,今天的人不必觉得它和历史一样与生俱来。
——又比如说“现代”。我们知道,现代包括韦伯所谓的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包括可以实现进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科学,包括保证人类精神的自由,包括维持社会秩序的民主,都可以归纳到所谓“现代性”中,它和“启蒙”有关系,它的核心理念包含了理性、科学、进步、自由、普遍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等。根据现代人的总结,第一是地方性让位于全球的普世性;第二是功利的计算取代了感情与神圣的崇拜;第三是政治和社会单位不再是宗族、家庭,而是个人;第四是人和人的关系不由出身、阶层,而是由现实的选择;第五是人定胜天取代了天人合一。所以,近代西方的启蒙,主要就是“除魅”,就是以理性怀疑的精神、科学实证的精神、个人和自由的精神,来反对宗教信仰和神圣崇拜,解除过去对于地方、家族、神圣、阶层的认同和迷信。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在这一框架中间被认识的。可“现代性”这个东西,现在,却有很多人在质疑和批判,不仅仅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全能的现代性很怀疑;包括一些很拥护现代化过程的人,也对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中一些问题很有警惕。所以,很多很多我们过去并不认为需要反省的东西,90年代后开始需要重新检讨和反省。
不仅仅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全能的现代性很怀疑;包括一些很拥护现代化过程的人,也对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中一些问题很有警惕。因为,这些常识的变化,涉及历史上的很多具体问题研究,比如说——
第一个,是你怎么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所以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都在这一判断基础上叙述,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反帝反封建,就成了一条主线,但是这是否就是一个惟一的历史解释呢?现在有人按照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按照权力与话语的理论,按照世界体系的理论,这么一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线索的评价和叙述好像就不同了。
第二个,是现代化与中国的社会组织。宗族的存在究竟有多大,它对民间社会的控制是否那么厉害,过去我们按照儒家经典的记载,总会觉得中国古代社会里面,王权、神权、族权、夫权,都很厉害的,以前毛主席好像都说过,四条绳索嘛。在中国,民间社会家族就是基础组织,包括西洋人也是这么说的,认为古代中国国家控制不下到县以下,宗族仿佛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社会,由士绅和宗族领袖形成中间层,它们构成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层,有时也成为对现代化经营的阻碍。但是,现在重新有人提出,古代中国,国家控制编户齐民的能力是渗透到基层的。秦晖有一次到我这里来聊,他说从长沙走马楼吴简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国家或者政府对于民众的管理已经很直接很细了,哪里有什么中间层?这个结论很大,因为这涉及到妨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主要力量,究竟包括不包括“宗族”这样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和历史上的“宗族”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对外关系,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合理的平等的,还是傲慢的俯视的?比如,近代中国的衰落,到底是清帝国的傲慢和自大,还是西方列强的野蛮和无理?是中国促进了西方的进步发达,还是西方冲击着中国使它开化?西洋人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对他们的态度是妨碍了中国融入世界,还是当时反殖民主义的一个必要坚持?这涉及到一个如何评价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看待近代进步观念、殖民主义、东西交流等等的大问题。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后现代历史学著作,就会对这一问题提出另一种解读。
第四个,是“五四”反传统的问题,到底“五四”是否真的是反“传统”,并且造成传统的断裂?或者还是“五四”只是构造了一个作为“箭垛”和“敌人”的传统,然后通过批判取得合法性,宣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结果传统并没有消失?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例
四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例
也许讲了这么久,还没有进入我们自己的专业。以前说秀才买驴,写契约写了三张纸,还没有到“驴”字。我们也有些这样,可能圈子兜得太大了,背景讲得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书归正传”。
我们现在以具体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为例。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那么,什么是文明?中国的文明观念和文明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中国尤其是汉族人是否一直就很文明?现在我们渐渐开始知道,许多现代人认为不文明的东西,在古代其实是没有这种不文明的感觉的;而古代一些很正当很文明的东西,后来却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可见所谓合理的、文明的、那些“理”、那些“文明”,是后设的,其实,古代人并没有现代文明的这些观念。可我们过去研究文史的人却以为,过去的中国人就是文明的,也是像我们这样理解文明的,从不反省这种关于文明的观念和规则可能是历史建构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通常历史书都告诉我们,中国古代人的道德理性很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不会有特别的极端的宗教狂热如残人或自残之类,很多书上都引用孔子“伤人乎,不问马”、“仁者爱人”来证明这种“文明”。但据学者们的研究,并不是这样的。在以后的课上我会介绍一个法国很有名的学者葛兰言,他就曾经在《古代中国的跳舞与歌谣》中讨论鲁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他追问:为什么在齐鲁盟会上,孔子要下令斩优倡侏儒?为什么杀戮了以后还要将他们“首足异门而出”?这种习惯怎么后来就没有了?而且到了宋明以后,儒家学者也好,考据学家也好,都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在《谷梁传》、《史记》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事情?这是因为,过去儒家有一个共识:孔子是圣人,圣人不会做错事,乱杀人,更不会那么不文明地杀人。这里对圣人的权威的信任就是一个常识。照说《谷梁》也是经典,它记了孔子杀人,为什么后来的人不相信?因为对“圣人”的常识更大,基础更深。所以,这就不能信。你看,这常识作为前提和基础厉害不厉害?其实,因为有了这些常识和观念作基础,写历史的时候,才常常会“省略”很多事情,这就逼得我们要像鲁迅《狂人日记》里说的那样,在字里行间去发现历史中被删减了的东西。
我们要像鲁迅《狂人日记》里说的那样,在字里行间去发现历史中被删减了的东西。再比如宗教的狂热。一般宗教史都说外国宗教或者未开化地区的宗教信仰有很残酷的自虐,有不雅观的性仪式,可是,我们仔细看,就会看到中国也不例外,北京有一个年轻学者雷闻,曾经写文章说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那里传来了“割耳剺面”和“刺心剖腹”的风俗,但是在隋唐的时候也被汉族人接受了,这能够说明古代人并不是那么爱惜身体,也曾经有过自虐的风俗的,对于幻想的信仰有时候比对于身体的理性更有力量呀。另外,杨联陞先生很早就写过文章,说到早期道教中就有一些很残酷的仪式,就是“涂炭斋”呀。道教徒在这种仪式里面,要把自己的头发捆起来,再用黄泥涂脸,涂过后,就不断拍打胸口,叫做“拍打使熟”,而且时间不是一天两天,是七天,冰天雪地也罢,下雨刮风也罢。这样的东西好像我们过去的文明史中并不讲,好像古代中国自从儒家一统以来,一直是很文明的;又比如传统的观念都认为,古代中国人对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对于异性的身体是有禁忌的,然而据我了解,在中国南北朝时,即公元4到5世纪前后,居然中国还有当着公众的面以男女性行为为中心的仪式,道教中称之为“过度仪”,如果这些仪式可以公开进行,我们反过来想是否那时人对异性的身体和性行为的观念并没有像我们过去想的那么严厉?过去对中国文化史和宗教史的那些判断以及观念,好像不那么可信嘛。
我们现在受到一些现代观念的影响,对“文明”总有一些固定看法,这些看法虽然是后来形成的,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想像和判断。其实,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什么是文明,各个时代可能不一样。我们现在受到一些现代观念的影响,对“文明”总有一些固定看法,这些看法虽然是后来形成的,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想像和判断。其实,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什么是文明,各个时代可能不一样。我们以死人的埋葬为例。唐代以来,受佛教影响行火葬,这在现在看来不是很文明吗?一直到宋代,大家看《水浒》,它虽然是小说,不过也有一些影子历史。比如里面武大郎含怨死后,是火葬的,所以才可以从里面偷拿一根骨头出来嘛,虽然小说是后来写的,但是还是反映宋代的风俗。宋代初期,看来火葬很流行,所以《东都事略》记载,建隆三年皇帝只好下诏,“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为了“厚人伦而一风化”,所以要禁止火葬,在整个宋代,这都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特别讲究文明的理学家,大力反对火葬,大家可以看柳诒徵1929年写的《火葬考》,因为在他们看来,文明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够随意乱烧。那么,这种土葬是否是文明呢?其实也未必然,只是古代人相信人一死不能复活,即使可以复活,也需要有肉体的基础,所以有饭含或玉含、有金缕玉衣、有高水准的尸体防腐技术,有重重棺椁,保存尸体的意义本来未必是尊重父母身体,但是被解释出来这层意思以后,就被赋予了“文明”的意思。大家再看,清人入关前后,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就都是火葬的,尹德文就写了一篇《清太宗皇太极火葬考略》,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1期上,但是,这是女真旧俗,是蛮夷的习惯,到了满族人稍微一“文明”起来,他就又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了,连《实录》、《会典》都不说这件事了,雍正皇帝还解释一番,说是战争时期,迁徙无常,不得已。可是,到现在,西风东渐以后,火葬又成了“文明”。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文明”要重新看待,对于文明史也要重新认识。我们现在总是相信,许多古代人是生活在儒家文明理念影响下的,但事实上,若回到原始资料重新了解,会发现事实不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知道的历史,其实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经过层层的过滤和筛选以后,历史把它想告诉我们的告诉给了我们,却把另一些东西遮蔽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的历史,其实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经过层层的过滤和筛选以后,历史把它想告诉我们的告诉给了我们,却把另一些东西遮蔽起来。于是,近几年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古代文明的一些现象,也在重新考虑一些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的评价。这些,实际上对我们的文明史提出一些严厉的挑战。这是一个大的变化。所以,90年代后出现开始重新检讨古代思想、文明以及哲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