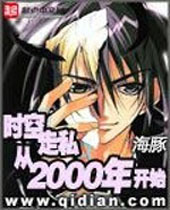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明以及哲学的历史,对大家习以为常的那套文学史、思想史和哲学史都开始了重新检讨,这些检讨主要是针对过去观念世界中的共识或前提,认为这些被当做常识或基础的东西不一定对,这就是“重写(文学、思想、哲学、艺术)历史”,这是90年代后整体的社会变化和观念变革所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关注重心与使用资料的变化
五文史领域:关注重心与使用资料的变化
90年代后,研究者的注意力变了,从过去传统的领域挪开,开始稍稍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变化,刺激了历史学的第二个大转向,就是文史领域中关注重心的移动。90年代后,研究者的注意力变了,从过去传统的领域挪开,开始稍稍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从重点研究国家、精英、经典思想,转向同时研究民众、生活、一般观念;从研究的空间来说,从重点研究中央、国家、都市,转向兼顾研究区域、边地、交叉部位。这好像连锁反应一样,再接下去,就引起了第三层变化,就是研究资料的变化。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过去习惯的资料就不够用了。过去历史研究者在资料上习惯于用普通的传世文献,它们固然很重要,但那主要是精英和经典,是传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做法。可是,现在研究领域扩大了,你就需要关注其他资料,因为这些“其他资料”在研究中现在用得还不太多,尤其我们研究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的人。比如考古发现中的各种简帛、田野调查中关于各种信仰仪式习俗的资料、边缘文献比如历书、类书、蒙书,甚至包括目录书、诗歌戏曲、工艺技术、天文地理,特别是图像资料。
大家都知道,20世纪初,当文学史、历史、哲学史作为学科建立以来,尽管许多人提出来种种看法,比如梁启超在关于“新史学”的文章和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著作中,对传统史学提出的质疑,说它们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里面,研究者的主要思路和目光都集中在精英和经典层面上,在不断的叙述中,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历史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图像,通过教科书,不断复制,大家都在这里面生活,于是习惯了这一套,这种图像让我们都觉得,历史就是这样。但是大家都忘了一点,一个人看东西时最看不到的是自己的视网膜,就像我们看电视时,常常忘记镜头的存在。事实上,那个图像是被镜头和观察者的眼睛一起重新构造的,可是,我们后人看历史,就以为这些叙述、这些记录、这些描述就是历史,于是历史就会变形。我常常要讲这样一个想像:一个人要是再活一百年的话,他回过头来会看到自己现在所经历的生活,和一百年后学者们写的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十年的历史会很不一样,写下来的历史和他亲身经历的生活是两回事,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如果想较真切地描述我们经历的历史尤其是社会生活史,与其用《新闻联播》一二三条,用大报的社论和新闻,用中央红头文件,还不如多用一些其他东西。如果要描述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心情的话,与其用大报的社论、政府的文件、精英的著作、学者的论文,还不如用现代流行的电视剧、所谓美女小说、广告、流行歌曲排行榜、政治笑话、俗谣谚、街头报摊、网络帖子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重建社会的场景,更接近生活的实际心情。如果要描述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心情的话,与其用大报的社论、政府的文件、精英的著作、学者的论文,还不如用现代流行的电视剧、所谓美女小说、广告、流行歌曲排行榜、政治笑话、俗谣谚、街头报摊、网络帖子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重建社会的场景,更接近生活的实际心情。1997年美国的非文学类普利策奖给了一个叫约翰·道尔(J。W。Dower)的人,他的获奖著作叫《接受失败》(Embracing Defeat),研究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生活和历史,用的很多材料就是这一类东西,它的真正重心是在讨论一个时代民众的“心情”和“感觉”。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开始有人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90年代以后,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学术界都出现了对社会生活史、一般思想史、大众文化史等等的关注。这才真正地改变了过去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的历史,你总是以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当然就只能围绕着“帝王将相”写历史,可是你把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大众观念当做历史的中心,当然领域、视野和资料都变化了。
关于新的关注重心和新的资料的变化,这两方面,我们这门课,还需要专门讲几次。所以,这里只是蜻蜓点水一样地说一说,以后再仔细谈。我想,这种研究取向的转变肯定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但是要说明一点,法国和中国之间,稍稍有一些时间差。从前,年鉴学派提倡“从阁楼到地窖”,将历史研究重心从上层政治转向下层生活,现在欧洲人已经又从“地窖转向阁楼”。从前,年鉴学派提倡“从阁楼到地窖”,将历史研究重心从上层政治转向下层生活,现在欧洲人已经又从“地窖转向阁楼”。但是在中国,因为过去过分将研究注意力集中在经典与精英的层面上,所以现在海峡两岸都开始往一般的、边缘的,但是又是普遍的影响很广的方向转化,今后是否也会从地窖转向阁楼,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就现在看,目前的这一转化的好处就是研究范围较过去的空间、范围、视野和资料都大了很多。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小 结
六小结
以上,我说到了基本预设的重新检讨和反思,研究领域的重心转移和研究资料的范围扩大,这就是我体会到的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文史领域的一些重要变化。这里的逻辑很简单,新的研究观念和思路的出现,一定会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新的领域和视野,又一定需要新的文献和资料,这是很自然的,只要稍有敏感的学者,在最近十年的文史学界都可以看到这种潜在的变化。我自己在做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也正是在努力追踪和适应这种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虽然并不普遍和明显,也未必能够成为主流,但我始终认为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的开场白,以后我们要一点一点仔细讨论。
【建议阅读文献】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4。
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1992。
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
黄俊杰《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学生书局,台北,1987。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1900年
第一讲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讲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900年,美国的鲁宾逊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新史学》,1902年梁启超也写了一本《新史学》,他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提倡民族主义的新史学。前一次课上,我们已经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这一次,我们就具体来讨论年鉴学派的意义。
这一讲之所以选用“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这样一个题目,我有两点要先说明。第一,我不是做历史学理论研究的,更重视理论怎样可以拿来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所以在这一讲里,具体地说,就是看看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能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文化史、思想史研究中,这是我想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用“对中国的影响”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实际上,法国年鉴学派现在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有一些影响,但影响还不是很大。之所以用这个讲法,更侧重在讨论,它在将来可能会发出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出现了新的趋向,虽然还只是在萌芽中,动静并不是很大,但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会时时提到中国学界研究的动向和情况。
1900年,美国的鲁宾逊(J。H。Robinson)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新史学》,这本书后来曾被做过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者——他在1924年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差不多同时,在中国人这里,1902年梁启超也写了一本《新史学》,他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学,提倡民族主义的新史学。这两本书都叫“新”的史学,叫“新”,就意味着过去的是“旧”,但是,新、旧不会一成不变,时间一长,新的还是会变成旧的。最近,就是2002年夏天,国内也开了一个会议,名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样看来,无论是鲁宾逊的还是梁启超的《新史学》,都已经变“旧”了,不然现在怎么会特意地提出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呢?
那么,你也许会问,真正的“新史学”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呢?也许,目前还不见得。不过,看看海峡两岸,倒也有一些新的动向。1990年,台湾创办了一个杂志,名字也叫《新史学》,至今已经十四年了,出版了十四卷,每卷有四期。它的发刊词中明确承认他们是受到注重经济、社会和心态文化研究的年鉴学派的影响。发刊词中说,20世纪只剩下最后十年,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酝酿之中,大凡这种时代,都会有新的历史学出现。那么,到底这个“新”是新在哪里?大家可以注意,杂志里有很多专号,比如关于社会医疗史的研究,身体史的研究等等,还有中国妇女史专号,不过这里的妇女史跟过去相比,有很强的女性批评的思路在里面,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女性史是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西方的视角和理论。还有性史专号,有关性的研究虽然很早就有,如弗洛伊德、金赛等等,但在历史学里面,真正受到强烈启发的是福柯以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性意识史》出版后,才形成了新的性史研究的视角。此外,还有宗教史、疾病、医疗文化专号,比如,有一篇论文讲到钩端螺旋体病在宋代如何蔓延,有的论文还讨论到疾病如何改变了这个地方的人口结构,改变生产和种植的习惯。这样的研究过去很少,乍一看觉得很新。大家要注意,这个杂志几乎囊括了台湾中生代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而经过十来年,现在,这些“新史学”的学者已经是台湾最有影响的学术群体了。
回过头来看看大陆,近些年也开始逐渐注重社会生活史、都市史、地理环境史、科技史的研究等等。比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和刘志伟,他们和美国学者萧凤霞一起做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的乡村史研究,厦门大学的郑振满和加拿大学者丁荷生一起做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都是试图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另外,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与历史评论》集刊,提倡社会史,显然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又比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一个社会史研究室,出版了断代的若干册社会生活史,在资料方面也做得不错。很多学者都开始了这方面的个人研究。天津师范大学也在做有关“经济社会史”的研究,还出版了一些论著,还有的年轻学者,也开始了医疗、疾病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像人民大学的杨念群、南开大学的余新忠等等。就以我周围的熟人来说,北京师范大学的赵世瑜一直在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像明清的庙会和社火之类,清华大学的李伯重也做过关于宋代节育观念和经济史的关系研究,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琦研究科技和社会互动关系,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连一直搞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外交通史的北大的荣新江也做了关于壁画中所见女扮男装图像的研究,很有些现在流行的性别研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