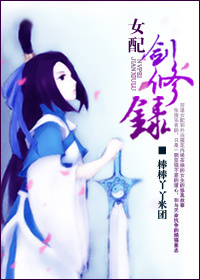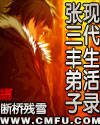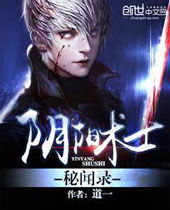妇女闲聊录-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在家,是九几年的事。他家柴也烧得多,他爸爸去捡柴。
他弟弟还没讨老婆,讨不了,穷,外号叫测量器。以前安电线杆,有人来测量,他跟着学,所以村里人就给他取外号叫测量器。
现在这家的大女儿十六岁了,去打工,修表,现在日子好过些。
村里有一个人,外号叫细青蛙,在武汉当鸡尾,染上了性病。
他是个光棍,快四十了,在武汉打工,老跟在〃鸡〃后头,村里人就管他叫鸡尾。泥工,长得不怎么样,又黑又瘦,主要是穷,房子倒有,家里有四兄弟,大哥二哥有老婆,三哥在黄石也讨了一个傻子,领了一个女儿。傻子什么都干不了,但她很爱那女儿,回王榨,谁抱都不给,别人抱,傻子就使劲哭。她在黄石嫁不出去,她父母就让她的几个哥哥,每人每个月给她一百块钱,不管嫁不嫁人都要给,但她嫁了人后就不给钱了,这男的养不了她,又不要这傻子了,又送回了黄石,那女儿留下来了,在大哥家养着,有五六岁了。
细青蛙一直在武汉,听说他染上性病,治不好了。
去年他大哥媳妇说她公公扒灰,其实是她自己挑逗的,她在家里经常只穿着一个文胸和一条三角裤。叫木菊,她后来跟人跑了,跟唱戏的跑了,上麻城。她跟我们村的细棍好,把她带回她娘家七天,婆婆家来人向娘家要人,娘家说,你们回去问问你们村的细棍,细棍只好到麻城把她带回来。丈夫要打她,她说别打了,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过不久,丈夫打牌赢了200块,回去一看,木菊又跑了。到现在还没找着。
木菊跟她大姐看上同一个男的,趁她姐夫不在家,这两姐妹就跟这个男的睡,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木菊自己是大哥的老婆,白天就跟二哥睡觉,跟小叔子睡,被人看见了。二哥的老婆最老实,回娘家了。
四季山有四大婊子,不是真的婊子,而是长得漂亮,有名,所以就叫四大婊子。其中有一个女的,她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女儿,身体不好,丈夫就把她卖了。在酒馆里,她丈夫下的蒙汗药,人贩子就把她弄走了。
卖到那地方怕她跑,在她脚板上钻了三个孔,用铁丝拴着,又生了个孩子。后来被解救出来,上了滴水县的电视,很多人都看见了,看见她脚板有三个洞。回来后她又在四季山山咀嫁了人,那男的腿不方便,比她小,她又生了两个女儿。
另一个婊子是我们王榨的,她交了个男朋友,男朋友上大学了,不要她,她就跳河死了。
我们结婚都不去登记,不领结婚证,现在年轻的也不领,但是发户口本下来,上面也有名字,他们要凭户口本上税。
有个女的嫁到我们村,她要跑,也不用离婚,就从男家跑到另一个男的家住下来,这个男的怕她再跑,赶紧去领结婚证,结果还是跑掉了。
别的村有一个男的,老婆老是跑,找一个,跑一个,又找一个,又跑一个。后来他干脆找了一个〃鸡〃,这个〃鸡〃也有丈夫,经常带人来打。这男的也是姓王,跟我们村同姓,就到王榨找人帮他打,找多了,干脆他就搬到王榨来了。刚才小王打电话来就是用他的手机打的。
我们村有个女孩,初中毕业,去深圳打工,摔伤了,手臂断了,回家养着。是夏天,天很热,我们大家都在树荫下乘凉,那女孩也在。这时候来了一个麻木,就是摩托车后面有座,像出租车似的,从县城到我们村是二十块钱。
那男孩从麻木下来,喊这女孩,他手里拿着三朵红色的玫瑰,要送给这女孩,女孩怎么都不要。她就是不要。那男孩呆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走了。
我们就说,人家送你花你怎么不要,这么远送来了。女孩说,你知道三朵红玫瑰代表什么意思吗?我侄媳妇说:代表我爱你。我侄子说:Iloveyou。大家都笑。那男孩到了河岸上,就把花扔了。他说:去你妈的!
我儿子去河岸玩,把花捡回家,他说这花多好看,扔了可惜。
第四章王榨的风俗与事物(1)
同一个村子,大儿子管父亲叫〃爷〃,小儿子叫〃爸〃。也有的叫〃父〃,〃伯〃。兄弟几个,老大的孩子叫爸为〃伯〃,最小兄弟的孩子叫爸为〃父〃。其他兄弟的孩子称爸爸为〃爷〃。
称母亲〃娘〃,也有叫〃姨〃的,也有叫〃大〃的。现在赶时髦,都叫〃爸〃〃妈〃了。
管爷爷叫〃爹〃。小姨妈叫〃细爷〃。大姨妈叫〃大爷〃。
细,就是小的意思,细哥,细姐。
老人都怕火葬。村里一个人娘家,有一个老太太,钻进人家的墓里,那人死了很久了,那里面是空的,棺材都已经烂了。她钻去,封好了墓门,再喝农药,结果没死成。
我们村里死了人,全都是土葬,没有火葬的。都说过了五一就统统火葬,都说,那烧得多疼啊,都怕。那好象是79还是78年,那段就要烧,那段时间真正烧。我二婆说,什么时候死,千万不要在这时候死,死了就挨烧。烧得多疼。她就偏偏这时候死。二婆就烧了。还有堂姐也是烧了。
有的自己家里父母死了,怕烧,就自己家的人,偷偷地埋在菜园子里。后来问起来,追查出来了,就去菜园子挖出来,再烧。那时候很严。
有一个乡的书记,可能是得罪人太多了,有的偷偷埋在茶园里,他就把人挖出来烧。后来,不抓这事了。他父亲死了,埋了,人家把他父亲挖出来,把棺材撬开,把人扔了。他们家又收拾,又葬了一次。葬了又挨弄出去,又扔尸体。只好再葬,用水泥弄死,扒不出来了。
后来又说去要烧。说是2000年要烧。后来说过了五一,那个老太太吓得就自己爬到墓里去了。老头老太太又慌了。七几年的时候,家家都有棺材,后来让火葬了,棺材就做了别的。现在又全都做起棺材了。现在又不烧了。
三十斤大米,一桶水,放大锅里把饭煮熟,不能有锅巴,中间要挖小脸盆那么大的洞,往洞放半桶冷水,放8两大麦芽,麦芽在沙滩上发芽,一寸长的时候不能变青,是黄的,扒出来放在河里洗净,在屋顶上晒干,一捏就碎就行,还要放在轧米机里轧。放了麦芽,还要放一点石膏。要把米饭搅凉,手放进去不烫。盖好,保持温度到下午四点,揭开锅还是那个温度,凉的就发酸,烫了也不行,上面的一层像水那么清,底下是饭。
再烧开,放进榨篮里,再放到糖凳上,用糖棍压。把榨出来的糖水放到脚盆,再倒进大锅,留一点糖水在木勺里,木勺必须是枫树木做的,不沾。用大火烧锅,水越来越少,锅边放一碗凉水,用来洗糖签,糖签沾糖水,拿起来一试,像小旗似的,这时候就能喝了,小孩子最喜欢喝,1块5半斤。
还要继续烧,又用糖签试,这就成了大旗。就能炒了,火放小,又用糖签试,一砸就断就行了。起到大子里。洗锅,把子放到锅里,盖好。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好了。
拿一根枫树棍,放在糖凳上,把米糖绕在棍子上,一开始是金黄色的,越拉越长,变成白色的,就好了。
三块钱一斤。一年做三四十次卖。一锅能缠二十多个饼。我们村就小王一个人做,他做得最好,很多人也做,做得不好。
我们玩龙灯跟电视上舞龙一样,龙里点着灯,每节里都有蜡烛,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任何一天都舞龙,晚上点蜡烛,是纸龙,到正月十五就燃掉了,叫〃燃灯〃。
你要是想发财,或想生儿子,你就挑头找人做灯,要连着舞三年,重做要花半个月,要是光燃掉纸,竹架子还在,只糊纸,两天就行。小王的弟弟挑头舞龙灯,舞了三年,结果就发了。正月十五晚上,举着龙灯从街上穿过,所有两边的人都可以用点燃的鞭炮炸龙灯,举
灯的人不许生气,要拼命跑,有的用毛巾围着脖子,或者用衣服打湿,或者干脆脱光。坏一点的人会用长鞭炮围在举龙灯的人的脖子上,或者把捻子去掉,把炸药翻出来点火哧你,但你不能发火。
玩灯要单数,不能双数,最短的有九节、十一节、十三节,多的有几十节,但都要单数。前面有一个联系人,叫〃引路的〃,还有一个小灯笼。进村前引路人要去问人,从哪边进哪边出,不能乱走,一个村的左边叫青龙,从青龙进,右边是白虎,要从白虎嘴出。引路的后面是龙灯,再后面是锣鼓,最前面有两个大鼓,后面跟着几个人扛袋,专门收礼物,或钱,或蜡烛、香烟,香烟给一条,龙香牌,白金龙、红金龙,红双喜,姑爷家就给红塔山,回来大家分,有一大堆。
要交公粮,用钱顶也行。水费,灌溉用水,共50多元。乡统筹,全部加起来要一千多。提留。生猪包诊费。牛包诊费。鸡包诊费。
防疫费,给孩子打针的。
线路整改费,每家128元。修路,每年都修,最多时每户300多元。民兵训练费,一年十元。
教育费。
电费,比北京还贵。饮用水,自来水费。水利费,做江堤的。大田上交,一年好几十元。
每年发一个手册,上头只有几百元,实际上不止,有一千多。
每年还有义务劳动,如果做不够,就得出钱,叫标工费。
每年都有人上访。交不出乡里就来抓人,法院就来封门,有人喝药自杀,村里人就把尸体抬到法院去。
(我在北京青年报看到报道,在四川邻水,每出售一头生猪,就要缴纳地税、国税、定点宰杀费、工商管理费、个体管理费、服务设施费、动物检疫费、动物消毒费、动物防疫费、清洁卫生费等十项税费,共93元。为了保证财源,一些乡镇专门成立了〃小分队〃对那些拒绝缴纳费用的农民给予二三百元的高额罚款。木珍说,在滴水县,杀一头猪要交120元,比四川高将近30元。过了几天,木珍的哥哥来,说不止收120元,多的时候收到170元。)
谷子到加工厂去加工,一边出糠,一边出米,老式的机器,有一个风扇。
要吃豆腐上马连店买。
榨油上很远,二十多里,他姐姐的油榨,榨得好吃,香,其实近一些也有油榨,半里地。榨油菜籽的油,一百斤油籽能出三十三斤油,到他姐姐那边能出三十七斤。十三块手工费,手工钱一样,我们去只收十块。我们几家人一起去,用手扶拖拉机拉去,每人凑点钱,买条烟,我们买两斤猪肉,我们那边的肉连骨头一起卖的,六块、六块五一斤,还搭一坨猪头肉。
切成片,放上盐、酱油、味精,一拌,过一会儿下锅炒,先炒熟,再放上蒜、青椒一起炒。
第四章王榨的风俗与事物(2)
唱戏有两种,一种叫庙戏,做庙,落成的时候,开光的时候,就唱戏。
一种是谱戏,修家谱,修成后,唱三年的戏。同一个曾爷爷的,每一家的老大,或每一辈的老大,发一个谱。修谱的时候赞助的也可以得到一本。赞助有三百、五百、一千的。
由一个人牵头,看有多少人,男的才进家谱,活的多少,死的多少。有一种说法,如果死的人或活的人漏掉一个,就对牵头的人不好,不是对他声誉不好,而是他会死掉,所以谁都不愿牵头。
连九十岁的老头都不愿意。
修谱专门有一个谱堂,在祠堂里修,或者盖一个房子,作为谱堂。
这次是楚斌牵头,他外号老爷。有一个管经济的,有跑腿的,一共六个人。94年开始修,95年修成,95、96、97年,唱了三年戏。
到县印刷厂印,经费分摊,男的每人三十,怀孕的未知男女的,叫旺丁,也要给三十元。马连店能照B超,女胎就打掉。
唱戏的钱,每人自愿给,别的村都来,好几个村的都来。发谱在哪天,唱戏就哪天开张,临时在稻场搭戏台,一人高,短木头从四鸡山砍,长木头各家出,唱完戏再还回去。木头还能用。唱几天要看钱多少。
马城县的戏班,楚剧。300元唱一本,有《方青拜寿》《珍珠塔》《天仙配》《反八卦》《乌金记》《罗帕记》《四下河南》《三世仇》《二子争父》《约罗女游十殿》《三堂审母》《安堂认母》《玉堂春》,反正你点什么他唱什么。
由牵头的人点戏。
把亲戚接来看戏,还要买菜,还有很多做生意的。十里八里路的都去接来,我去接大爷和细爷(即大姑和小姑)。接,就是上门一趟告诉她们,邀请的意思,到时她们自己来。如果是父母,就可以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