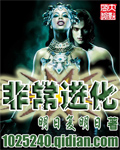非常对话-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它的一种情况是,一批进城的干部纷纷和农村的结发妻子离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丈夫进城后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土生土长的原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男人的门面要靠女人的装点,就与妻子离婚;二是农村来的妻子确实适应不了城市的新生活,继续留在丈夫身边彼此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负担甚至是折磨,结果只好选择分手;三是因为工作需要而组织上动员离婚,例如有个进城干部被分配做外事工作,在许多外交场合需要夫人作陪,可是他在农村的妻子竟是个小脚妇人,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只能动员他们离婚。
徐兆寿:最后这种情况倒是听着让人震惊。为了工作,为了集体利益,可以完全不把个人的命运的利益放在眼里。听起来是冠冕堂皇,但实际上违背情理的。那么其他人的离婚呢?
刘达临:更多人的离婚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相互交织。由于丈夫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活,和妻子长期分居,夫妻之间的感情自然日益淡薄;何况,有许多妻子本来就毫无感情可言,他们之所以结合,要么是战争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要么是父母的包办所致,是童养媳、换亲、指腹为婚等婚姻陋俗的受害者,因此,这类婚姻的破裂在所难免。同时,革命胜利,部队进城,许多城市女青年、女学生对革命干部怀有崇敬、仰慕的心理,甚至有追求的行动,这也是一些干部和原配妻子离婚的外来诱因和添加剂。
以上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并不能说明认为“离婚非好事”的传统观念已经消除了,而只能说这是一种“革命需要”。一些干部为了革命多年征战,流血牺牲,好不容易进了城,过上了和平生活,理应对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予以照顾。在那时时代,“革命需要”是压倒一切的,组织上对这一类的离婚一般是予以宽容的。
徐兆寿:这使我想起过去那些王朝的开国元勋们,一旦他们大功告成,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就大肆纳妾。当然,原配夫人是不会放弃的。同时我还想到战国时期的百里奚认妻。百里奚之妻杜氏领着儿子流亡到秦国,此时百里奚已经是秦国的相国。杜氏车上望未,不敢相认,只好到百里奚府里洗衣,她因为会琴鼓,便设法在堂上唱歌,歌曰:“百里奚,王羊皮!……今日富贵忘我为?……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怎么能说这些妻子就没有为共和国立下过功劳呢?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那些居功者可以为了“革命需要”而抛弃妻子,而这些被抛弃的妻子又向谁诉怨呢?
刘达临:这的确是那个时代不能回避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是传统的道义,一方面是人性的要求。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彻底取缔了一夫多妻制,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是不允许这些功臣纳妾的。怎么办呢?说简单一些,两个人过不到一起,难道还要让他们一起过吗?这恐怕又是不道德的。当然,对于他们的离婚,多数人是持反对态度的。当时还涌现出一个妇女自发组织的“秦香莲”告状团,上京告状。那时,离婚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如果依靠组织,组织认可,的确比较宽容;如果违背了组织的决定,那么传统观念和一系列的大帽子足以可以把人压死,“王疯子”王近山中将的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
徐兆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本来在莫斯科和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相恋,但在刘少奇的安排下,和巴彦孟结了婚。“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尽了苦难,但巴彦孟也和她离了婚。可以说,这是第二次离婚浪潮中的一个例子。
刘达临:第二次离婚浪潮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70年代末形成的,其原因大多是出自政治压力和对政治扭曲了的婚姻现象的改变。很有悲剧色彩的是,仿佛是上次离婚浪潮中的女方报仇似的,这时的离婚大多却出自女方,男方接受,双方都别无选择,是当时的强权政治导致了心灵的扭曲,是一种恋态社会的政治压力下形成的畸形的离婚现象。
这里面也有几种情况:在那个极端严酷的年代,一些人突然从革命同志被打成政治异类,他们的妻子“划清界限”的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一些人为了子女的命运和前途,也忍痛把离婚作为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甚至有一些丈夫今着眼泪动员妻子给“组织上”写离婚报告。这是只有在中国十年浩劫中才会发生的怪现象。
另一种则是非常恶劣的,少数女子一看政治形势,就对丈夫落井下石、见风使舵,寻找新的依靠。当然,也有一部分确实死亡了的婚姻,政治运动恰好提供了最有效的解脱的借口。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当时上山下乡的政策造成的。有些青年的父母本来是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变成了“黑五类”子女,被驱赶到农村去,他们认为自己一辈子要在农村生活了,于是就和农民结了婚,在农村安家落户,生了孩子。政治形势一变,这种婚姻就跟着变了。这种婚姻本来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属于委曲求全的性质,夫妻双方的条件不平衡,当政策变了,有些人无法把配偶及子女的户口落到城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最后离了婚。在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被驱赶到农村去由于“落难”,在农村结婚成家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最原始的需求——成家、生活、性和生殖。父母的政治问题一旦得到了平反和改正,他们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中去了,原来在农村缔结的婚姻很少不解体的。人们称这种婚姻为“文革婚姻”。
第四部分第60节 119。1万对离婚的夫妻
徐兆寿:前几年流行着一首歌《小芳》,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不忘怀。”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当时,他们也是有爱情的,只不过这种爱情是降到农村里了,降到了尘土里,他们成家也恐怕是在这种基础上,而不应该是最原始的需求——生活、性和生殖。政策恢复后,他们回到了城里,生活又发生了变化,又恢复了他们原来的生活、理想,他们的情感也变了。这是生活的变化导致的,而不能说农村人就没有爱情。《小芳》道出了那个特定年代很多人的内心,歌里有一种忏悔,有一种永难抹去的伤感。这正是那种尘土里的爱情在他们心里的烙印。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可能又重复了他们父辈的道路:乡下结婚,进城离婚。无论怎么说,在价值意义上,它仍然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悲剧。
刘达临:那种婚姻是不相配的,没有相同的志向和情趣,没有共同的观念,这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说纯粹是一种原始欲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里有一种文化的观念在起作用。但是一旦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他们的婚姻也就会随着解体。
徐兆寿:第三次离婚浪潮应该是人性的复苏。
刘达临:总体上可以这样说。第三次离婚浪潮发生于80年代和90年代,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也是在新《婚姻法》颁布以后。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新《婚姻法》对离婚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这个时期的离婚案明显增多了,在20年期间,离婚率从1980年的4%左右增加到90 年代中期的11%左右,直到1998年才首次下降——即使如此,1998年离婚的夫妻仍然有119。1万对。
徐兆寿:离婚率增长的现象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些人开始惊呼婚姻家庭将要解体,道德将要崩溃。
刘达临:有些人总认为离婚率的增加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过去,社会总把离婚率低看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把离婚率高看成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之一,但是怎么现在中国的离婚率也不可遏制地大幅度增长了?其实,不能认为稳定就一定是好事,要看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稳定。在政治上,万马齐喑的“稳定”决不比思想活跃、百家争鸣来得好;在婚姻家庭问题上,被封建枷锁捆住的“稳定”也决不比人们享有离婚自由的“动荡”为好。在奴隶制社会就没有离婚现象,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要求离婚的权利因而离婚率很低,显然,这都不是什么优越性。
徐兆寿:1984年7月,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妻子王永贞听到法院的离婚判决后,在法庭上服毒自杀,保持了永远“贞洁”。也就是进入八十年代时期,人们的观念还是没有多少改变?
刘达临:在八十年代时期,离婚仍然是被看成一件不光彩的事,离过婚的女人被人看不起。
徐兆寿:寡妇也比离过婚的女人有尊严。
刘达临:在80年代,有些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是不要离过婚的女青年的。一些妇女特别是农村的妇女仍然是“要离婚,毋宁死”的态度。王永贞就是这种观念的牺牲品。在1989年到1990年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曾对7971例城乡已婚夫妻提出了“女人离婚是否不光彩”的问题时,其中回答“是”的,城市夫妻占11。1%,农村夫妻占12。9%;回答“否”的,城市夫妻占72。5%,农村夫妻占65。2%;回答“无所谓”的,城市夫妻占14。6%,农村夫妻占21。5%。可见,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80%以上的民众都认为妻子离婚并没有什么光彩,年轻一代在这方面的观念则要更开明一些。这就是进步。
徐兆寿:在第三次离婚高潮中,除了离婚数量的增加外,还有什么特点?
刘达临:一是离婚由女方主动提出的多了。据1992年最高法院统计,主动提出离婚的有70%是女子,还不包括协议离婚在内。二是协议离婚的人数逐年上升,过去那种“拖死‘陈世美’”或“不见血离不成婚”的现象正在迅速减少,“好来好散”、“不是夫妻还是朋友”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1997年夏天,报纸上登过一则离婚广告:
离合皆缘分,聚散两依依。我们结婚3年,在此友好手分之际,谨定于×月×日×时,在××歌厅举行告别鸡尾酒舞会,恭候新朋旧友光临。
电视台也进行了采访。丈夫说:“如果我们的昨天有一些遗憾的话,今天已经没有了,将来也不会有。我们又重新拥有了无怨无悔的日子。”妻子也说:“没有离婚礼仪,彼此也许还有怨恨,因为找不到一个在亲友面前表示醒悟、忏悔、宽容的机会。今天,是我们难忘的时刻,因为有了昨天,才有了这个流光溢彩的今宵,有了这个流光溢彩的今宵,就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他们互相交换了离婚戒指以后,彼此举杯祝福,接下来以朋友的身份,跳了一曲《友谊地久天长》,把鸡尾酒会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这个极具浪漫气氛的离婚仪式,实际上对现在婚姻观的极好的诠释。它告诉人们,离婚也是一件喜事。
徐兆寿:这的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在这两个特点中,尤其第一个特点引人注目。更多的是女子提出离婚,它暗示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这是否与西方“性解放”文化涌入中国有关?即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关?
刘达临:有一些关系,但主要是与社会的离婚观念和妇女的经济基础有关。一方面,离婚不再是一件让人蒙羞的事,妇女完全可以因不合理的婚姻而提出离婚;另一方面,妇女逐渐地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可以不依靠男人而活着,这样,妇女就可以能够承担离婚的后果。
第四部分第61节 男人处于被动局面
徐兆寿: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对离婚率的不断增长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我们发现,越是高收入、高知识结构层的女性离异者越多。
刘达临: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使她们对男子的人身依附关系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自身素质的提高又使自信心空前高涨,对配偶的要求也提高了,于是对低质量的婚姻状况当然不能满意。与此相对照的是男性世界变化的缓慢,这种性格角色发展的相对停滞,使男性在婚姻失败中承担的责任不仅不再具有以往的价值,而且容易让女性轻视。
徐兆寿:这么说,今后离婚的“受害者”,即最大的伤害者倒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了?
刘达临:不应该说男人就是受害者,只能说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