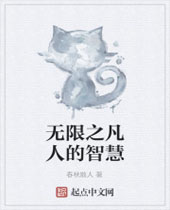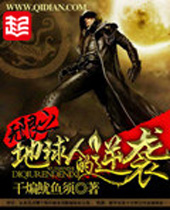�й��˵��Ը�-��3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ط��Ƿ����꾰�����ǰ�����ҵ�������ġ�ۡ�������й���������־��û�б������κ��й���Ϣ��������ʵ�������ܸı���ʵ�������������Ƿ�֪������£��������������ܼ�������ʹ��Ȼ������Щ��ʵ��Ҳ����֤����ȡ����Ч�ľȼô�ʩ���������Ϊ�й���Ӧ��ʲô���ӣ���һ���£�����ϸ�۲�����ʵ������ʲô���ӣ���ȫ������һ���¡���
�������Ǻ�������й������ڵ�����ײ�����������������ʵ�Ļ����̹��ҡ�Ҳͬ�����ڡ���������е�ʧ������Ϊ����û�ж���һ��ʵ��������ȷ�Ľ��ۣ�Ҳû�н���ϵͳ�ıȽϡ�����ȷ���������������ò�������������Ϥ����������ʮ�����ޣ����������������������Լ��Ƚϰɣ�����Ҫ�������ѡ����������ƫ��������֤�ݲ��������£���Ҫ����Ϊ�й��������ġ������Ƚϣ��������ٿ��Կ���������������Ե��dz�����������δ�����й���Ե�ȴ�dz����ڰ���������ȥ������������ߺú���˼һ����ζ�����ʵ���������ô��ɵ��أ���
�������ظ�һ�飬�й���Ҫ�ĺ��٣�ֻ���˸�����ġ�Ҳ����˵��������һ�����������ı��������˸����˳���һλ�����ĸ�������ң�˵���������ĸ���һ������������ֱ���߹����й���˭�������������ˣ���
������һ������һλӢ�����ҵĴ��ǣ��ڽ�β�����������ӶԸ�ȥ��������ɷ�����д�������������������ҡ�����ʿ��һ������Ա����ֻ��ÿ���������������һ����ͥ���ˣ���֪������һ���������ˡ��������������������һ��������ϸ�塢���������˽���ż����ض�Ϊһ����ɴ�����֡���ֻҪ���ҿ������ɴ���ҿ���˵������������������С������۵ĸ����У���һ��������ɫ�İ���һ������ʮ���꣬���ࡢ�������ɡ�������������ʱ���ǽ�����ʱ���������������ĵ����ӣ���������������ӣ������ǰ��죬���Ǻ�ҹ����δ���ֹ�һ���ִٲ��ʵ����ۣ�һ�����ͷ������ƣ���һ����˽�ľ�ֹ�������ݸ��еİ������֤����ʿʱ���������ȥ����ô������һλ�и���Զ������ݰ����Ů����˵�����˹����˹����һλ������������ʿ������
�������������������õĹ��ӣ��������������������������������������ټ��������������ٸ���¼������ǧǧ����Ϊ������֪�ġ�ÿλ��������֪��һ����ȫ�����������˵����ӣ���Щ���߿����������Լ��ľ��������������������ӡ���������������Щ�����أ����ǵĶ������Ժδ������Dz�ϣ�����ֻ��ɣ���������������֮������ȷ�ţ����ʹ�й��������������ӵ�����������������һ�����˹��һ�����ˣ����ڵ��·��棬����һ��ΰ����漣���ȵ��ҵ伮������Ԣ������漣��Ҫ���κ������ƶȣ���������������Ĺ��ɣ���ʥ������˵���������ǵĹ��ӣ���֪�����ǡ���������㹻��ʱ���������ս�����������ţ������ģ�����ȫ���ˣ��Ժ���Ҳ�����и���Ĺ��ӡ�����ʹ�˵��������ӵ��˼��£����ҳ����������ط�������������������������һ�С����ĵؿ������й�����Щ����֮��ʹ�������Ƶ�������Ҳ���ò������س��ϣ��������������й�������
�������й��ĸ������ϣ��������ֲ�ͬ��̬�ȡ���һ��û��Ҫ�ĸ��Ȼ�������е��й��˶������룬�������в����й��˱�����һ̬�ȡ�ijЩ���˽��й���������Ҳ������Ϊ���ڶ����ĸﲻ���ܳɹ��������ġ����ڵĸĸ���δ��ʼ���ͱض�����������ϰ��������л����˽��һ����ˣ����������ֱ��۵��۵���������Ϊ�����Ӵ���й����г��ĸĸ�����ľ����ע�����ʹ�临��һ��������ϣ�������������û������ǰ�����������һ�۵���Ե��۾ݲ��㡣��
������������Ϊ���й�������Ҫ�ĸ����Ҳ���ܳɹ���������Ϊ������Ĺؼ������Ժ��ַ�ʽ���иĸ�ⷽ�棬Ҳ�м��ֹ۵㡣��
��������������Ե������ǣ��й��Ƿ��ܹ����Ҹ��£���ʶ���ĸ�֮��Ҫ���й����μ���Ϊ���й���ȻӦ�����Ҹ��¡������������ۡ������һ�������У�����һ�����Ҹ��µ����ӡ�д���۵Ĺ�Ա��Թ�ڵ�ijʡ�İ���ɧ����������˵�����ɳ�һ��������Ա�������أ���������������ʵ۵ġ���ѵ���͡�������Ȼ��ϣ��������ǿ�����ķ�ʽ�̻����գ��������ס�����һ�����������������ԣ��Ի����̴�����ԭʼģ�£��ڸ����˵ĵ���Ʒ�з��棬�Բ�ʧΪһ������ϣ����óɹ��ķ������̻�ʧ�ܺ�û�б�İ취��ֻ�����ȥһ�����ٴν���ͬ����Ŭ�������ڵľ����������һ������Ȼ��ʧ�ܣ��¼��仯����������ɣ�ȫ��Ŭ�����ữΪ��Ӱ���Ǹ�ʯ�ȣ��۱�����˵�Ԣ���ѳ�ֱ�����һ�㡣��
������Ȼ������Ч�����DZ��ϣ���ڿ�ģ����һ�㣬ǰ�����������ۣ��������ᣬ����ָ��Ϊʲô��õĿ�ģû�в���Ԥ�ڵĽ������ԭ��������������ʹ������˽������������е�������������磬ɽ��ʡǰ��Ѳ����֮�����ݱ���˵��������ȡǿ�����Ĵ�ʩ��ֹ������ʳѻƬ����ֹ������ֲѻƬ���������������ж�����������ͨ������أ�û��������ϣ����������֪���κ�һ������ˣ�����������������й��˲�֧�����ĸĸ�����ܲ����ϣ����й������ϣ�������Ϊ��������һ���й��ˣ�������λ�Ӻ�ְ���ѵ���ͬ����е������ߣ��������Ŀ��ȷ��֮�����ִ�����ǰ�����⣨ֻ�DZ����ϵģ����·�һֻè���ڸ�¥�ϣ���Ҫ��������������λ��Աһ�����Σ�������δ��ʼ�ߣ�������Ѿ���ʼ��ˣ�һ���վɡ���
�����й����μ�Ӧ�û������Ըĸ������ϣ�����ⲻ�����ţ�Ҳ��Ϊ��Ȼ����Ϊ����֮�⣬��Ҳ����ѡ�����һλ�����IJ��е߹�Ա���˽��ˡ����������еĿ��µ��䵭�������ۡ��������ּ��˵�����ϯ��˵����ʹ�ϵۣ�Ҳ�ƿ�ʩ����������֪�����ڡ��ĸ�ķ������棬��������Ͱѽ��ȷ��Ԥ��ˡ��Ͳ�������̸���й����Ͽ���ͭ��¶�����ıײ�ʱ˵����ͭ��û����ȫ����֮ǰ�����ϱ��벹���˿ڣ�����ƽ�ȶԴ�������������·������������ӽ����εĺ�����ʩ����һ�仰���й����뿪���������������Ķ���֧Ԯ�������������һ���̣�һǧ���ʱ�䶼��������*��
������ͼ�ĸ��й������������������������ڴ����촬�����Լ�Ԧ�ĺ�ˮ�ͺ����ʹ��һ�л�Ϊ����һ�Ρ�ʼ�ڲ����ڻ����ڲ������Dz���ʹ����ǰ���ġ���
�������˺��ڱ��������֮�䣬��һ��ת�䣬���Ƕ����οͻῴ��������һ��������һ���������һ�뱻��ˮ�����ˡ���ˮ��һ����һ������������դ������˩���ϵ�һ����«έ��ɣ�������ˮ������������ͷ����ƾ�紵��ɹ���Ӵ��л��������࣬��Χ����Ұû���κ�������ˮ����ʩ������һ�������ưܵĵ۹��о����й���һ�侭����ԣ�����ľ���ɵ�ֻ�н���ľȫ���������������ܷ���ѿ���й�����ڲ��ĸ��Dz��ܳɹ��ġ���
��������ǰ���������ҹ㷺��Ϊ���й�����ͨ�����롰���ˡ����������������������ϣ��û�ж�����ʵ�ĸ��ݡ�������Ҫ�����ڱ�����פ����������ʮ�����ˣ����ǵ���Ϊ���ѵ��й������˶��������Ӱ�죿���ң����˱������ǣ������Ĺ�ϵ�������й������������й��������£���������ʲô֤�ݿ���ʹ�й������ţ����Ƿ�չ�Լ����ҵĶ����ܱ��й��˸ĸ�Ķ��������У���Ȼ�й��Լ����ڳ�Ϊһ�ɡ�������������æ��������������֮��Ĺ�ϵ������ȡ����ȴû�뵽�����������ڡ��Ӷᡱ�����������ڽ��е��½̻�����ˣ���ʹ�й�Ҫ�ĸҲ����ͨ���⽻;����������
����*���ѹʵİͲ����������ζ��Ļ������Ϊ1890��8�±�����ۡ������һƪ����֤ʵ�ˣ����Ͽ���ִ�����ʱ����˹������������������˵�������Ǵ������зǷ����ɣ���Ա�Ǻ��¶�������Ȩ��������������������һ���취�����ǵͼ۹����Ƿ����ɵ�ͭ��ʯ������Ч�����������ǵĶ����Ͷ�����һ����Ҳ���ܵ����˵Ļ�ӭ������Ϊ�����ַ����ȿ���ʹ�ɿ��������У�Ҳ����������������ṩ��ڡ����������ʵ�ֻ����˰����������¡���¼����������
�������۸����У�Ѳ������˵��ÿ�¿��ԴӷǷ��ɿ����������һ���ͭ��ʯ����������Ǯ��ֻ���������ͺʹ��ס����������˵������������������dz��������⡣����
�����ʵ۲�����ÿ�춼���յ�Ѳ��һ����Ա�Ļ㱨�������˹���Υ��������ط����ֲ��Ҷ����ǣ��������ͺʹ�����ʹ�������㣬һ���Ǯ������ʹ���ǽ���͵�ɵĿ������������ӻʵۼ�������Ա���۹��IJɿ�ҵ�š��dz��������⡣���ֺ�Ҫ��˰���𡰼�¼�ڰ�������
����Ҳ���˼��ţ��й�������Ҫ������ʴ��ͥ��������Ҫ���ɽ���������ó�ף���Ҫ���DZ˴��మ����ͬ���㡣ֻ����ҵ��������й�������鵤��ҩ������Ҫ����Ľ����ڣ����͵Ĺ�˰����Ҫȡ��ͨ��˰��������ʮ��ǰ������Ҳ������������Щ�۵㣬��ʱ�й����ѳ�ֵ������Ĵ����Ǻ������������Dz�û��ѧ�ᡰ���ɽ������͡��˴��మ�������ֵܡ������������˵�й��IJ�Ͳ����������ϸ���������ij�̶ֳ��ϻ�������������ڵĻ����
������ҵ��Ϊ�����ĸ����ֶΣ����ֵ���������ġ�����������������Ϊ�ĸ���ֶΡ��ִ�����ѧ��ΰ�����ǵ���˹�ܰ��˶���Ϊ����ҵ�������˵���κ�����������֪��������ͷ����ʹ��������֪����������һ��������Ⱥ��������һ����ͷ�����г������ֻ�Թ����Ը����ʲô��Ȼ��Ӱ���أ��Ŵ���Щΰ�����ҵ���ң���������õĹ��ң��෴���������ġ����ǵ��ִ��̳��ߣ�������ȫ��ͬ�������ܹ�����ó�ף���ȫ��������ԭ����ɵġ��о仰˵�úã���ҵ��ͬ�����̣�Ŀ�����ޱߣ�����ҵ�������ʺ磬�������ɫ��һ�ߡ���
����ֻҪ��һ������½�����ˡ���Ⱶľ�����˽��ū��ó�ף���һ�ֲ����ɻ����̹�������ģ���Щ�����ݵ����ѣ��ѵ���˵������ҵ��û�и������������𣿡�
���������˽��й���״�����ѣ�Ϊ�й�����ҩ��Ҫ�����渴�Ӷ��ˡ�������Ϊ���й���Ҫ�������Ļ��������Ŀ�ѧ����÷��˹����˵�ġ��������������й�����������ǧ�����ʷ�����ǵ����Ȼ���ɭ����Ѱ��ʳ��ʱ������������������������ˡ�ֻҪ�ǵ������ܳԵĶ���������������ù���������������ܸĸ��أ��Ļ�����˽�ģ����������������ǿ�����ң��������㡱���������й������������Ժ����Ļ���ȴ�������Ū�ͷ����Եļ�Ц������й��Ļ��Դ˲��ʵ����Կ��ƣ��ѵ���������й������ﲻ���ͬ�������ˣ���
������ѧ������Ҳ���й���������Ҫ�ġ�������Ҫ���ֿ�ѧ�������۹�DZ�ڵ���Դ������������ؿ�������һ�㣬���õĽ��������ῴ�ø�����������տ�ѧ��һ�������ڸ��Ƶ۹��ĵ���״������Ҫͨ�����ַ�ʽ��ʵ���أ���ѧ�����ִ���ᷢչ��ϵ����ܵ�ѧ�ƣ�Ȼ������ѧ֪ʶ���й��Ĺ㷺���������й��˻�������ĵ����ֶ����ѵ�������ĸ�������Ͳ��ᴫ���µġ����벻������թ�뱩����Ϊ�𣿰����й��˵������Ը�������������������ִ�ըҩ���䷽�����ҶԻ�ѧҩƷ���ӿ��ƣ��ѵ����ǻ��ܹ��Ű�ȫ�������𣿡�
������չ����������������ζ�Ž��߱������߶ȷ�չ�����ʳɹ����������������͵���������ĸ����漣��������Ϊ��������й�������Ҫ�ģ�Ҳ������ȫ����Ҫ�����Ӹ������е���·����½���ϵ��������ˡ��걸���ʵ�ϵͳ���������У�������ΪͨѶ����ĵ绰��籨һһһ��Щ�������õ����й������Ա�־����
������Ҳ��������֮����δ���͵��뷨��������������·�������У�������·�������������кܶ���ܵ�Σ�գ�������ˮ��͵�����ȵȡ���ô�����������ķ�չ�������������ϵ�а������·�ܱ�֤��Ա���������ϰ�ij�ʵ�����Dz��Ƕ����������ǵ�һ�¡����������εĹ�����·�����ߣ��ɶ��������ߣ��Ҳ������ø�����ˡ��������������Լ���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