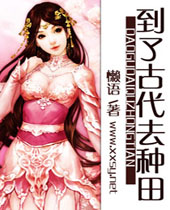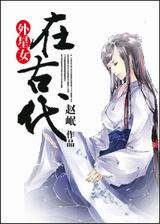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义夫节妇”的头衔。这种人物形象本身内蕴的思想与作者给予解释的矛
盾,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这个剧被收入郭汉城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
悲喜剧集》。
《玉搔头》、《奈何天》、《凰求凤》思想远不及《比目鱼》。《玉搔
头》写明武宗微行大同,托名威武将军,与妓女刘倩倩之间的情事;中又贯
以王守仁、许进辅佐武宗平宸濠事;《奈何天》写一不知书、多财富的奇丑
男子阙里侯,连娶三美妇,均因其丑而逃避净室,题扁额曰“奈何天”。后
阙里侯力行善事,感动神明,变为美男,终于全家和谐。“奈何天”有人生
有命无可奈何之意。此戏说教意图明显,作者在第二十三出借阙里侯第三妇
之口说:“你们看戏的里面,凡是有才有貌的佳人,嫁不着好丈夫的都请来
看样。就作才思极高,不过象邹小姐的了;就作容貌极美,不过象何小姐罢
了;就作才貌兼全,也不过象我吴氏罢了。都嫁了这样男人,任你使乖弄巧,
也不曾飞得上天,钻得入地,可见红颜薄命四个字是妇人跳不出的关头,况
且你们的丈夫,就生得极丑,也丑不到此人的地步。大家象我一般,都安心
乐意过了一世罢。”显而易见,这番议论意在要妇女屈从于命运安排的“妇
道”。《凰求凤》写才高貌美的书生吕哉生被众女追逐——许仙俦、曹婉淑、
乔梦兰三美争一夫,格调不高,劝人止淫止妒之意甚明。
李渔第三期作品为《慎鸾交》、《巧团圆》,写于寓居金陵的后期。《慎
鸾交》写吴中妓女王又嫱、邓惠娟择婿从良事。秀才华秀与王又嫱于择交慎
重,不轻易相许,但一旦订交后终不负心;秀才侯隽与邓惠娟一见便信誓旦
旦,而终却背弃。剧中华秀是李渔理想中的风流与道学合一的形象。他在第
二出华秀第一次上场时,就让华秀讲了这个道理:“我看世上有才有德之人,
判然分作两种:崇尚风流者,力排道学;宗依道学者,酷诋风流。据我看来,
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
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这话实际上是说:读书人寻花问柳,自是名士风流,
只要做得适当,就能既保住正人君子的美名,又可享受倚香偎翠的艳福。这
真是为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创造的绝妙的行为依据!《巧团圆》一
名《梦中楼》。写姚继自幼失亲,后几经周折巧获团圆事。“奇缘奇会,情
节幻甚”。
纵观李渔十种曲,或美化士大夫风流韵事,(如《意中缘》);或努力
将文人狎妓与道学名教统一(如《慎鸾交》《玉搔头》);或鼓吹、歌颂封
建的婚姻道德(《奈何天》《怜香伴》《凰求凤》),思想都很平庸。即或
《比目鱼》之类的有积极意义的动人的爱情戏,也不免被作者落后的思想所
笼罩。所以,虽然李渔剧作语言通俗生动、结构比较洗炼,艺术成就较高,
但总的说来并不引人入胜。
第三节 李渔的剧论
李渔的戏剧理论主要见于《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
人们将此两部称为《李笠翁曲话》。《闲情偶寄》作于李渔晚年,结晶着他
一生创作及舞台指导的实践经验,因此许多都是“折肱之语”,发语中肯,
论证深透,至今仍不乏指导意义。
李渔论剧,比较全面,涉及到编剧、导演、舞台演出、观众心理等许多
方面。说它体大思精,也未尝不可。他的词曲部,分结构、词采、音律、宾
白、科诨、格局六部分;《演习部》分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五部
分。其中每部分又各有分论,就某一侧面详加阐发。下面仅撮其要点作一介
绍。
1。结构第一。李渔说:“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他认为,戏
曲不同于诗词古文,它是专为登场搬演故事的,所以,就要特别讲究结构。
如同建房,“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
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论剧重结构,乃李渔首创。由
于我国戏剧为戏曲形式,所以,人们从来都首先看重音律。虽然李渔之前也
有人注意到结构,但从未如此强调。
在怎样组织结构上,李渔认为,应“戒讽刺”“立主脑”、“减头绪”、
“脱窠臼”、“密针线”、“审虚实”。等。其中“立主脑”、“减头绪”,
是说要突出主要矛盾,删除与情节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繁芜枝节及“旁见侧出
之情”。此说颇有针对性,对明代以来一些传奇越写越长,枝蔓杂芜现象很
有纠正作用。“审虚实”讲艺术虚构问题;“戒讽刺”说不用戏剧作人身攻
击;“脱窠臼”指情节及其安排上新颖不落俗套;“密针线”指情节结构上
要前后照应,不出破绽等等,都是与结构结合起来阐述的。有不少精彩之论。
2。戏剧语言“贵浅显”“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贵浅显”、
“戒浮泛”是说戏剧语言应通俗和个性化;“重机趣”意为戏剧语言之间要
有内部联系,要有人情味,趣味性,全剧要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忌填塞,
要少用事用典。李渔认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
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
不贵深”,所以,戏剧语言应“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
但他同时强调,“浅”不是粗俗,而是“意深词浅”,作者应富有文学修养,
广泛读书,“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 。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
书? 。孩童所习之《千字文》《百家姓》无一不在所用之中。”但“至于形
之笔端,落于纸上,则宜洗濯殆尽”。即要将民众的生活语言与各种书本文
字融汇贯通,“于浅处见才”,既通俗,又有文学色彩。而且,要“语求肖
似”,“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
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 。”。阐议颇精,几近今人之论。
3。提高说白地位,使与曲词等同。李渔说:“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
我国古典戏剧为戏曲形式,故一向重曲词而轻说白。如徐渭说:“唱为主,
白为宾,故曰宾白”。而李渔认为:“曲之有白,? 。犹经文之于传注;? 。
如栋梁之于榱桷;? 。如肢体之于血脉”。“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无限
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词而生出无穷话柄者,是文与文自相触发? 。”所以,
李渔认为,不仅戏中宾白数量可增加,而且同曲文一样,要认真推敲,“声
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简”,“字分南北”、“文贵洁净”,
“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时防漏孔”。李渔此说亦为创见,对我国
戏剧形式的发展,大有裨益。
4。格外重视戏剧的审美特性,立论紧密联系演出。李渔说:“填词之设,
专为登场”。为此,他撰演习部,专谈登场之道。《词曲部》中诸论,也都
密切联系舞台演出立论。如在结构上,他主张“减头绪”,原因之一就是为
了使三尺童子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他抬高宾白地位,亦是要以说
白帮助观众了解剧情,因唱词不易听懂。他批评《牡丹亭》中某些曲文过于
典雅艰涩,观众难于听懂,只能“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他要求少用
方言等,都是从剧本能否搬演于台为观众理解为依归。他并以自身体会为例,
讲剧作家编剧时必须考虑演出效果:“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
复以神魂回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在理论上明
确提出写戏就是为了演出。这对于明藻绘派以来一些文人刻意追求文辞博雅
深奥,把剧本变成案头文学的现象,有极强的针砭作用。
此外,李渔对人物关系的真实感及情节发展的逻辑性上,在戏曲音律上,
乃至于演员的艺术修养上,都有许多真知灼见,此不一一赘述。
以上着重介绍的是李渔剧论中与文学联系较大的部分。李渔这部剧论,
多讲艺术而少谈思想内容。但并不是他忽略戏剧的思想性。在《闲情偶记?凡
例》中,他说:“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
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剧论中仅有的一点涉及思想性的字句中,也
全是封建伦理的一套。他剧论所体现的这种特点,与他剧作的高艺术低境界
的一般状况是吻合的。
在一部戏剧文学史中,用一节篇幅介绍李渔的戏剧理论,足可见其地位
之不凡。李渔之前,亦有不少戏剧理论论著,如元代芝庵的《唱论》,明代
吕天成《曲品》、王骥德的《曲律》等,闻名于当世的有十数种之多,但如
赵景深先生所说,这些曲论,“或囿于声腔,或详叙故实,或泛评剧作,或
划分等第,理论家们虽于音律拥有专长,却缺乏丰富的舞台经验,与社会尤
少广泛接触。”《李笠翁曲话》是在我国民族戏剧土壤上生成的戏剧理论体
系,它把剧本文学与舞台表演全面结合起来,对我们今天的剧作家、导演、
演员亦都具有指导意义。从文学角度讲,他所提出的编剧理论,今天仍给人
以启迪。
第四节 吴伟业、尤侗等剧作家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卒于清
康熙十年(1671),江苏太仓人。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江左三大家”
(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之一,诗歌成就颇高。钱谦益称他“以锦绣为
肝肠,以珠玉为咳唾”;《四库提要》说他的诗歌“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
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明崇祯帝、清康熙帝都对他的才华倍
加赞誉。
吴伟业生活于明清两代。他早年深得明崇祯皇帝的赏识。崇祯四年
(1631)会试时他曾遭人诬陷,后由崇祯帝亲批试卷,他才得以高中一甲榜
眼(第二名),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之后又奉旨归娶,极为荣耀。在崇祯朝,
他仕途一直是春风得意:崇祯十年(1637),迁东宫讲读;十二年,又迁南
京国子监司业;十三年,升中允谕德;十六年,升庶子。为此,他对明王朝、
对崇祯帝感激涕零。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入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
他悲痛欲绝,“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救护劝止。之后,他又曾在福王朱由
崧的南明朝官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不合,居官仅两月便辞归故
里。吴伟业在明朝所受的荣宠和封建正统思想,决定了他与新朝的不合作态
度。因此,明亡后,他闭门不与世相通十年,屡受官召而不赴。但他又性格
软弱,未能坚持到底。顺治十年,“诏举遗佚。荐郯交上”,在清政府的“敦
逼”及父母流涕相求下,他不得已而应召入都,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顺
治十四年,以病辞归。
作为受过先朝“厚恩”的封建正统文人,吴伟业一直把仕清看作是“失
节”的行为,他常为此痛悔自责。他的不少诗都流露了这一情感:“忍死偷
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还不如”“误尽平
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在六十三岁去世前的遗嘱里,命埋葬时将他
的墓石刻为“诗人吴梅村之墓”,不愿以入清后的官名相称。
吴伟业的戏曲作品主要就是反映了他的自责自悔矛盾彷徨的心境、是“伤
心痛哭之调”。他有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等。这
几部剧都是“案头之曲”,以抒发情感为主,他自己说“一唱三叹,于是乎
作焉,是编也,果有托而然耶?果无托而然耶?余亦不得而知也”(《〈秣
陵春〉序》)实际上,都是有所托的。
据顾雪堂《梅村先生年谱》说,《秣陵春》作于顺治九年,吴伟业四十
四岁时,其时,正值吴伟业应清政府之召出山的前夕。有人说该剧是吴伟业
读罢夏完淳吊南京陷落的《大哀赋》后,“大哭三日”提笔写就的。如此看,
《秣陵春》剧反映的正是作者应召前夕那种矛盾、彷徨、无可表白的心情的。
《秣陵春》以南唐功臣之子徐适与宠妃的甥女黄展娘之间的爱情故事为
载体,抒写了作者作为旧朝宠臣欲隐不能、欲出不忍、终于忝食新朝俸禄,
但又顾念旧朝恩眷的复杂心态。剧作男主人公徐适是作者这种心态的传达
者。在剧中,徐适是南唐后主李煜的旧臣徐铉之子,对南唐旧国怀有眷念之
情。剧中他出场时已是大宋统一后的第十个年头了,他因“家国飘零、市朝
迁改”而“浪迹金陵,放情山林”,不愿与新朝合作。尔后他到冥界做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