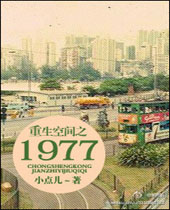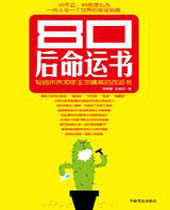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面貌。在当下的戏剧环境里,表演是最没有方向感的。一方面是舞台上随处可见的虚假的现实主义,另外一方面则是近乎装神弄鬼、不知所云的表演方法。表演是需要艰苦训练的,被认为现代主义戏剧大师的格罗托夫斯基所崇尚的“圣洁的演员”都由大量的表演训练累积而成的。在越来越多的舞台剧演员被电视剧吸引走、然后又以电视剧的表演方式来演戏的时候,舞台表演的质量自然在总体上不堪一击。在田沁鑫的《赵平同学》中,演员都很年轻,经验有一些,技能都很一般。田沁鑫并没有刻意拔高这些演员,而是因势利导,让演员在舞台上找到了一种放松的、自然的状态。而且,田导演在这部戏里还创造了一种融洽的观演关系,营造了良好的剧场氛围。从戏剧开头时所有演员站在观众面前向观众问好一直到表演结束,整个剧场一直荡漾着一种亲切友好的观演氛围。
在20世纪的戏剧理论中,剧场空间是个重要的命题,但如何捕捉“空间”稍纵即逝的感觉却是很难用理论说得清的。而田沁鑫在这部戏里,非常自如地创造了友善的、让人舒适的剧场氛围,正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说明。
戏剧:商品、艺术与“民间”民间的力量(1)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递增,对文化的支持力度也逐年递增。自2002年起,经文化部和财政部研究论证,“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开始实施。“精品工程”是指国家每年设立4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10部剧目,支持包括话剧、京剧、舞剧、音乐剧、越剧等地方剧种,希望以国家之力,打造出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各类精品戏剧。精品工程设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2002~2006)是在5年内投入2亿元资金,打造出50部舞台艺术的精品。在“精品工程”的大力推动下,许多在1980年代以来遭遇重创的国有院团似乎起死回生。只要这个院团能够创造出符合“精品工程”的作品,就可以得到几百万元的政府资助。我在2003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同行对祖国大陆的这一举措羡慕不已。“精品工程”实施到现在,也的确以强有力的财政手段,支持了许多重要作品的面世、演出:比如说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话剧《商鞅》(2002~2003年度),梨园戏《董生与李氏》、黄梅戏《徽州女人》(2003~2004年度)、舞剧《云南映像》、话剧《生死场》(2004~2005年度)等等。而我想“精品工程”在支持剧目演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此次以国家的力量支持舞台演出,使得许多长久不从事戏剧演出的院团,看到了制作舞台演出的意义与价值,从而能够更专心地投入到戏剧生产中。因此,有许多常年不在舞台上出现的剧种,比如说梨园戏、粤剧等等,都重新以良好的面貌进入观众的视野。这一举措,刺激了各个地方院团的创作热情,带动了许多省市的戏剧发展。
但重奖之下或许有的是勇夫,但不见得出的了艺术精品。任何一种奖励措施其实都是后发性的,并不能决定创作的成绩。精品工程的实施,的确是繁荣了文化市场,而且它在制度建设上也比以往任何的评奖项目都要完善。不过,由于“精品工程”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这也使得它的标准必然要做到“领导认可、专家买账、群众拥护”参见《以最大努力求精品工程的最大效益》,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访谈,载《2002~2003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论评》,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这也就决定它在选择作品时折中的态度。另外,“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用于创作的投入,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显然过于奢华的舞台美术装置方面,追逐外在的华丽而非剧本以及表导演方面的艺术内涵的充实与提升”傅谨:《建构舞台艺术的国家形象——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心得》,载《艺术评论》2004年第10期。。这一倾向,一方面是对创作带来了伤害,另一方面,也使得戏剧制作成本逐年上升。从长远来说,对于戏剧这个目前还很弱小的文化行业来说,是很不利的。
这里面有很多悖论的因素:一方面,政府以巨额资金资助戏剧生产,自然是有助于戏剧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入的加大,也就使得这一行业水涨船高,提高了戏剧的制作成本,自然为小本经营的民间戏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政府的资助又不可能贯彻、深入到戏剧生产的所有方面,民间戏剧又必须在政府支持的产品之外为戏剧生产提供补充。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个悖论,是使得戏剧生产达到平衡、有序的状态、使得戏剧生产全面发展的关键。自然,这个矛盾很难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但在2005年,政府与民间都在这一方面做出各自的努力。尤其是民间戏剧,在寻找自我生存途径的过程中,为戏剧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2005年,围绕着这一话题的最热门的讨论却是民间戏剧遭遇的一次重创。2005年9月,北京地区唯一一家由戏剧界的内部人士自掏腰包、小本经营的剧场——北兵马司剧场宣布关闭。很快,这个剧场就被中央戏剧学院租赁,民间戏剧再次让位给院团戏剧。
北兵马司剧场作为民间戏剧的重要阵地,一方面是起到了剧场的作用,策划组织并承接了多场演出;另一方面,这个剧场笼聚了大量的民间戏剧人,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气质,成为民间戏剧活动的重要场所关于北兵马司剧场的详细情况我在《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中《体制、市场与戏剧美学》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赘言。。因此,这个剧场的关闭在2005年9月间成了媒体关于戏剧的最重要新闻。一时间,北兵马司剧场的倒闭几乎成了京城大小媒体(其中也有一些其他省市的媒体)必须探讨的话题——这情形有点像是年末岁初出现的郭德刚相声。人们围绕着这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剧场的关闭做出了种种诊断。集中起来不外乎如下三点意见:一是政府文化部门的政策缺失。在戏剧发达国家,针对低成本的、具有实验性质的非商业演出,以及一些民间的非职业戏剧活动,都具有相关的保护政策,或者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或者给予政策上的便利。因为非商业的实验演出以及非职业戏剧,一方面是在戏剧艺术的推进上做着探索,一方面是在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这些活动自然无法与商业戏剧抗衡,也自然无法与有着政府大力支持的院团戏剧相提并论。而在我们这个戏剧不发达国家,在民间戏剧刚刚起步的脆弱阶段,却缺乏有力的保护性措施,这使得北兵马司剧场在勉强支撑了3年以后终于宣布解散的重要原因。二是戏剧主体即戏剧创作者自身的问题;这几年民间戏剧创作并不景气,缺乏好作品,戏剧生产的软弱无力,也就自然在源头上断了剧场的生路。如今,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期创下小剧场演出佳话的生力军如孟京辉等人,日渐远离了小剧场,而新的年轻戏剧工作者,却并不具备像孟京辉那一代小剧场创作者不依赖任何体制、单打独斗的创造力,无论是在生产方式上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不具有创造性。这也难怪像“戏逍堂”这样以广告运营商的身份进入戏剧生产领域的团体,以长时段的运营策略就可以轻易地垄断住人艺实验剧场。三是经营管理不善。民间戏剧在2000年前后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期,并且带动了许多民间戏剧人加入这个行列,从这些人中间涌现出了傅维伯、袁鸿这样的制作人,开始从事独立的剧场经营,这的确是件开拓性工作。但是,运作一个剧场与运作一个剧目的差别很大,能策划制作演出不代表一定能经营好一个剧场;而且在2000年前后院团演出基本处于停顿的阶段,在2000年之后,政府的大量投入,精品工程、大量官方的戏剧节等,这些都在无形中给民间戏剧提供了许多压力。面对不同的社会条件,在经营剧场的问题上,民间戏剧人似乎还没能找到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虽然2005年北兵马司剧场的关门,使得民间戏剧人一片悲声,但可喜的是,这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北兵马司剧场关闭前后,在上海出现了两家剧场:都是民营剧场,可性质却不尽相同。一家剧场名为“海上剧场”:这个剧场以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上海实业集团为背景的。上海实业集团在2005年开发了一座名为“海上海”新城的楼盘,开发商力图以“新文化地产”的理念来打造这个项目,在楼盘中附设剧场是其中的一项计划。据说这个小剧场很豪华,内部装修就耗资300万元,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上海实业集团在打造好这个剧场之后,就把剧场交给上海戏剧人张献、唐颖夫妇,让戏剧人负责具体经营工作。张献、唐颖夫妇在接受这个剧场之后,即在2005年底策划了名为“越界”的“海上剧场后现代表演艺术展示季”。该项目邀请了来自荷兰、奥地利以及上海本地的舞蹈团体,以富于“越界”精神的舞蹈剧场开启了海上剧场的演出活动。显然,这个剧场的出现为实验性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戏剧:商品、艺术与“民间”民间的力量(2)
与此同时,在上海还有一家名为“下河迷仓”的戏剧空间对公众开放。下河迷仓的经营者王景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1980年代即在上海的一些话剧演出中担任过舞台美术工作,1990年代以后,虽然不在戏剧院团,但一直热心于戏剧建设。2000年,刚从美国回来的王景国怀着对百老汇戏剧运作体制、经营方式的羡慕,以及对国内戏剧市场理想主义的憧憬,在上海肇嘉浜路上承租一栋上下三层的楼房,并用了一楼整整一个楼面,打造了当时名噪一时的“真汉咖啡剧场”。一些重要的戏剧作品,比如说赵屹鸥导演的《情人》、张献编剧的《屋里的猫头鹰》、女性版的《等待戈多》等陆续在这里上演。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这个剧场也一直申请不到剧场证,也就无法正常地从事营业性演出。“真汉”在维持了两年之后,也面临了和北兵马司剧场相同的命运,不得不关门歇业。但王景国并没有因此放弃民间戏剧的道路。在经过半商业、半艺术地经营了两年真汉咖啡剧场之后,王景国认为,如果把商业与艺术放在一起做,哪一个方面都做不好,还不如把艺术和商业彻底分开。从2004年起,王景国在上海龙漕路租赁了一处有上千平方米的厂房,取名“下河迷仓”,开始其彻底地非商业、非营利的剧场实验。“下河迷仓”或许算不上正规的剧场,只有简单的舞台与灯光设施,能够为演出提供基本设施。下河迷仓不经营商业演出,而是向上海的民间剧社、业余戏剧人开放,只要申请都可以在这里排练、演出——而且还是免费的。显然,这里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已经没有任何商业经营的意味了。王景国彻底地把自己的商业工作与剧场划清了界限。更为重要的是,下河迷仓不仅是个演出场地,而且它也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王景国在租赁了下河迷仓之后,吸取真汉咖啡剧场的经验,剧场本身不以商业为目的,但他以下河迷仓为基础,在上海市民政局申请创办了“下河迷仓原创俱乐部”。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性质,以民间学术组织的身份,接受捐助,吸收资金,以非营利性的实体的方式自主经营。显然,在经历过“真汉”的失败之后,王景国一方面在思考艺术与商业的关系,一方面也意识到艺术的发展也必须在资金来源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如今,“下河迷仓原创俱乐部”的成立,充分显示了民间戏剧的正在逐步完善自身的自主性,这或许是民间的力量得以维持、壮大的根基。
戏剧:商品、艺术与“民间”政策的保障
就在民间戏剧自主发展的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政策上做了适当的调整。2005年11月11日,文化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声称要鼓励、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发展。这份《意见》是继2004年7月文化部新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颁布之后,深化《细则》的具体方法。2004年《细则》的颁布,开放了营业性演出的主体资格;而《意见》的发布,则意味着政府为演出资格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基础。首先,《意见》明确了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地位和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