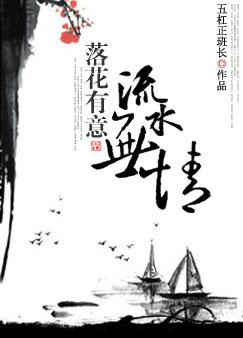高山流水-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是欲。许许多多的言情小说恶俗不堪,更有人公开提倡肢体写作、胸口写作。他们所迷恋的新创作,读者却斥之为挂羊头卖狗肉的伪文学。分析伪文学泛滥成灾的原因,主要是这班舞文弄墨者社会责任心的缺失。他们不明白,这些文字,只能写在私人日记中,或者是封存于法庭档案内,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着文学的旗号公开发表的。那些所谓的小说,一旦公之于世,便是对公众社会人文精神的亵渎,是不道德的行为。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首先便是出自这种对于公共社会的尊重,对人类社会的关心爱心。凡是受爱戴的作家,都是他先爱别人。人类社会的点点滴滴,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世乱民危时,他“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世道安定时,他“白日放歌须纵酒”。作家的心与读者的心系在一起,他的作品自然就表达了读者的需求,受读者的欢迎。现在有不少作品,对社会漠不关心,纯粹是个人的自恋,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既然写的是你个人,或是小圈子的喜怒哀乐,而你的这些情感又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那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来跟你一道消受呢?大家不读你的文章不买你的书,岂不顺理成章吗?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还源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珍重和爱惜。文学创作历来都被视为神圣的事业,“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数易寒暑”,“清贫冷寂”,这些字眼,过去常见之于对作家的介绍。李贺的负囊觅诗,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二句三年得”及“推与敲”,欧阳修的怕后辈笑骂,还有许多的“一字师”、“半字师”等等,都是文坛诗苑中的佳话。王实甫累死在《西厢记》修改的书案上,曹雪芹十载披阅五度增删书未竟而人已逝,这些故事常令后世肃然起敬。前辈作家之所以有这样执著的社会责任心,是因为他们珍重自己所做的事业,将它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但近年来却流行一种叫做“玩文学”的口号。文学创作是闹着玩的事,文学作品是玩出来的。持这种态度,能出传世之作吗?有的更宣布,他存心要写垃圾作品,更是匪夷所思!难怪现代人都不想当作家了,一个思维正常的人,谁愿意去与垃圾生产者为伍?
作家的社会责任心还与他的理想、信念紧密相连。这些年来,我们好像突然间进入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一切都量化为金钱功利,整个社会弥漫着浮躁焦虑的气氛。大家都在忙忙碌碌,都在奔走钻营,正所谓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思索”被挤压,“理想”、“信念”也被视为迂腐空虚而很少被提起。其实,一个没有信念的人是很可怜的人,一个没有信念的社会也是很卑微的社会。作为对人类社会极具敏感力的作家,不仅应是一个有信念的人,而且他的信念要美好而崇高,还要带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才是。
第五部分作家的社会责任心(2)
我们中华文化就是很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前面说过,在中国哲人的心目中,人应当像圣贤那样的生活,社会应当是天下为公。事实上,人非圣贤,社会也永远不会没有私财私产,这种人格和社会状态,只不过是中国哲人心中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中华文化最可宝贵的精华便在这里。三千年来,中国士人一直将它视为心中所守护的神祇,对它高山仰止,明知不能及却心向往之,明知不可达而勉力为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因为这个理想的至善至美而有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中国士人就因此丢掉它的话,中华文化拿什么来做它的灵魂?世界古代有四大文明,其他三大文明都衰落了,惟独中华文化世代延续,并不衰败,在历经坎坷后正在倔强走向复兴,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作为其灵魂,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回顾中外文学史,凡为人类奉献出不朽作品的作家,无一不怀抱理想,而他们的理想又无一不是美好而崇高的。这一方面是只有美好崇高的理想,才能成为指引社会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只有在美好崇高理想的鼓励下,作家才能激发对人类社会的强烈责任心。
人生中的善与恶是同时并存的,人类社会的活与乱也是同时并存的。作为人类精英中的一部分,作家有更多的义务,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张扬人性中的善良,鞭笞人性中的丑恶,从而促进人性的升华;去批判社会的混乱,护卫社会的整治,从而导引社会的和谐。作家应让自己作品的读者,得到的是疾恶好善、厌乱趋治的感悟,而不是相反。我以为,这便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心。这种为古今中外一切优秀作家所共同拥有的社会责任心,在今天,似乎更有重提的必要。
陶东风:请问唐浩明先生的,您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打着文学的旗号,公开发表,我想能不能稍微具体地讲一讲标准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历史上好多作品被判决为堕落的邪恶的,但是后来历史又证明那是很好的作品。谢谢。
唐浩明:文学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很难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也是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纯粹是一些个人的隐私,而不是引起人类共鸣的情绪,或者是那些东西只能是引诱人走向堕落,不能使人行为趋向于真、善、美,这样的东西是以文学的旗号发表的。但是这个标准是每个人去掌握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掌握。也有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很多作品出来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作品,当时被认为怎样怎样,后来看法变了,我想这也是一种正义。还有一部分认为是好作品,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作品不好,我想再怎么久的时间,也不会由坏变好的。
听众:我想请问一下唐浩明先生,有一本杂志叫《萌芽》,它的新概念很出名,而且现在出版很多的少年作家的作品,您认为这些少年作家是否有社会责任心?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可以说是不太成熟的,您认为青少年看了他们的作品之后,能否培养出来您所说的社会责任心?
唐浩明:现在有很多少年的作家,这些书,很对不起,我都没有看过。我个人觉得,这些作家可以是非常天才的诗人,但是也写了一些很长的长篇小说,实际写出来传世,我对这个持怀疑态度。但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以整个社会和人生作为表现的主题,12、13岁就会写传世之作,我表示怀疑。
秦伯益:我是比较喜欢看书的,最近一两年经常关注畅销书的排行榜,每个月都更换。前20位的,我发现最畅销的四类书,一类是领导和名人的书;第二类是吃喝玩乐的书;第三类是男女老少的书:爱情书和延年益寿的书;第四类就是坑蒙拐骗的书,脸皮怎么厚一点,心怎么黑一点等等这是四类书。今天唐浩明先生提到的社会责任心,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当前一个时期的问题。整个历史上,我觉得文学有高雅文学和媚俗文学的区别,高雅文学是要吃苦的,但是真正流传的是高雅的文学,鲁迅活到现在,要不关在监牢里面继续写,要不顾全大局不写了。我相信很多文学家是想写当代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的限制无法写。另外媚俗也是难免的,人总是要活着,作家要靠文字艺术的,他总要靠市场的。所以现在两个互动,读者引导作者写什么,作家看读者看什么。作家保持良知的话,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受清贫,一种就是你先有一个立足之地,当官也好,搞企业也好,然后你把你的主要经历主要兴趣放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今天唐浩明先生的发言又是一篇战斗檄文。有一些让它在地摊上畅销吧,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又名邓云生,1946年生于湖南衡阳,197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大前身)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在近20年的编辑生涯中,主要从事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编辑出版的主要图书有《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20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被称为“晚清三部曲”。《曾国藩》被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并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杨度》一书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及优秀长篇小说奖。先后获全国首届中青年编辑、中国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南省首届优秀专家等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现为岳麓书社编审、湖南省作协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五部分“智慧也是一种美”
——在中国海洋大学“科学•;人文•;未来”论坛闭幕式上的演讲
王蒙
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能够在短短的这么些时间里聆听近三十位科学家和我的文学同行们的演说及相互之间的提问与讨论。这样的好事,这样的快乐并不是我们经常能够得到的。毕淑敏女士讲了人生幸福的几个例子,我们中国文人也有中国文人的,我还是用“快乐”吧,幸福呢,我觉得稍微“酸”一点,而且它是受俄文的影响,俄国人喜欢讲“幸福”,其实在英文里它讲“happiness”;也差不多。孔夫子总结的快乐一个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个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论坛的作用就是能“学而时习之”,而且能够看到远方的朋友,另外就是“三人行必有吾师”,还有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几样快乐如今在我们的论坛上都具备了。这样的好事并不是经常能碰得到的。
尤其,由于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备教育的人,所以我听到我们的科学家的讲演,瞻仰到他们的风采,看到他们的身怀绝技的那种自信,那种富有冲击力的知识,我就感觉到,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光明,一种提升和丰富,一种美,就是一种善。我觉得正是知识里充满了人文的精神,而无知才是扼杀人文精神的。所以我长了那些知识以后,我确实愿意做你们的学生。我觉得“绝了”。(鼓掌)这样的学习机会,这样的学习气氛实在太好了。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除了学习以外也有一些碰撞,也有些质疑,我觉得质疑是所有的学科前进的一种动力。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质疑又不断解决和改善自己的知识能力与道德自觉的历史。也许可以说成是一个发展的进化的历史。但是,人们对发展和进化这个词也充满着质疑。科学上好像是在发展的进步的,而且先进的东西在取代落后的东西。譬如说,好的电灯可以取代煤油灯,但是文学和艺术就看不太清这种发展和进步。我们就无法说我们今天的作品可以取代《诗经》,可以取代李白、杜甫,或者可以取代《红楼梦》,不但取代不了,我们仍然自惭形秽,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人们不但质疑科学,人们也质疑文学,如果说科学主义是值得反思的,那么文学主义呢?我觉得陶东风教授(也许他不是故意的)不无讽刺地提到了我们国家也有文人进入领导核心的时候,他举的三个人,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伯达,如果再加一个艺术家的话,就是江青。用文学艺术的方法来处理国计民生或者是处理环境污染的问题,是不是会有一种最好的效果?所以,也可以质疑文学,甚至可以质疑历史,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历史是不是进化的?譬如,我们谈到“满意”,我刚说到量化,就是陈祖芬讲的那个量化的那些故事,我真是大开眼界。最近我还看到人们在分析,这也是西方国家喜欢量化,还有一个什么词叫“满意度”,就说现在虽然这个社会发展了,可是人们的“满意度”是多少多少,大概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的标准。我也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统计的,可是我的“满意度”可不是60年代的样子,因为上个世纪60年代我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连读书的权利几乎都被剥夺了。所以我的“满意度”就绝对不是相当于60年代,而是一百倍,二百倍,五百倍,一千倍于60年代,这就是文人说话,他可以从一百说到一千,不需要做很仔细的测算。
有时候我觉得人会被自己的能力,被自己的创造,被自己的革新和自己掌握的手段和可能性所吓住。质疑科学,对科学感到恐惧,古已有之。我可以想像当科学家说地球是转动的时候,当科学家说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的时候,人们感到的那种恐惧,那种震动。因为他已经有的


![小桥流水人家[完结+番外]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