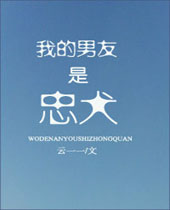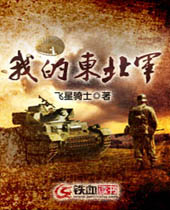我的梦想在燃烧-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即使在东方文化的内部,在这一点上,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也是大异其趣的。印度有泰戈尔这样歌唱爱情的诗人,但当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却遭到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嘲笑,笑他天真,笑他单纯。然而,我在泰戈尔的作品中却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因素。泰戈尔以爱为出发点,渴求人和神的汇合,企望人神合一而抵达理想的境界。他信奉“诗人的宗教”,其道德基础就是“爱”,爱人生,爱大自然,爱民众,尤其是穷人和劳动者。
泰戈尔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颅清爽的吹过的凉风。清晨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容脸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37
“你以你的爱使我伟大,虽然我不过是许多随波逐流的俗人中间的一个,颠沛在世间浮沉无常的恩宠中。在古往今来的诗人呈献贡礼的地方,在拥有不朽之名的恋人,遥隔不同的时代互相寒暄问好的地方,你给我安置了一个座位。市集上,人们在我面前匆匆经过——他们绝对没有看出我的身体因着你的爱抚而变为珍宝,他们也不知道我的身体里怎样承载着你的吻,犹如太阳在自己的球体里,承载着神火儿永世普照。”38
然而,中国当代文学中我却很少读到这样健康纯朴的爱情。我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中国人失去了爱的能力,还是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惊心动魄的爱情?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过美好的爱情。《诗经》的爱情、《孔雀东南飞》中的爱情以及梁祝的故事。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作家放弃了对这种纯粹的爱情的寻找、发现和书写。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我没有发现过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他最得意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残酷和血腥。他甚至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改编成芭蕾舞上演。据说,在票房的意义上,这出芭蕾舞剧在中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除了让张艺谋发了大财之外,只能证明他丧失了阐释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要的前提条件。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莫言的问题与张艺谋极其相似。在《檀香刑》中,我发现所有的人物都是人格扭曲、缺乏爱的能力的人。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塑造这样的人物,更为关键的是作家采取何种态度来塑造。加缪写《局外人》,也是写一个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但是作家本人的价值立场十分清晰:加缪认为,他要在没有温暖的世界上点燃一堆柴火,他要在没有爱的生命中加入爱的催化剂,他要在阳光消失的夜晚讴歌那“地中海的阳光”。
另一方面,文学是不是只能描写现实生活中那些畸形的、扭曲的、邪恶的感情和欲望?即使现实生活中没有那种美好的爱情形态,文学家是否有责任、有使命来为我们创造?正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不论大海还是荷马——只有在爱情中持续”,假如现实生活中没有了爱,文学中也没有了爱,我们的生存质量就必定会降低到一个极其可悲的地步。当文学家和诗人也丧失了爱的能力以及描写爱的能力,我们还有希望吗?
阅读《檀香刑》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顾城杀妻并自杀的事件(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顾城迷在为杀人犯辩护,同时把责任推卸到谢烨或者英儿的身上)。我发现,那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生活、我们继续目前的写作,类似于顾城那样的诗人还会出现,类似于顾城杀妻并自杀那样的事件还会上演。
文学高于生活。像《檀香刑》这样平行或者略低于生活的作品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它绝不是第一流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像《檀香刑》这样的作品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了。然而,在新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的第一轮评选中,《檀香刑》却以全票名列榜首。我不得不怀疑名单上那些名声显赫的文学评论家们的审美趣味、知识结构和价值立场。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指出:“莫言是农民流氓英雄的孜孜不倦的歌手,他的言说成为贯穿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线索,帮助我们窥视文学的秘密进程。”3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及其创作提供了文化史的重要资料。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极端缺乏并深切期望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唤醒人类身上残存的神性、挽救人类身上堕落倾向的文学;将爱、同情和悲悯贯注到我们生活中,将阳光、火和露水投射到我们生命中的文学。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这样的的方式生存在永恒之中。有关于阳光,它也许是不朽的一种反映,是‘持久’,是一种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使得你不能察觉的持久。”40
注释:
1《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48页。
2莫言《后记》,《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3页。
3莫言《后记》,《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6页。
4莫言《后记》,《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页。
5《莫言与〈檀香刑〉》,参见李潘《真不容易》,西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1页。
6《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359页。
7《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62页。
8参见《酷刑:人类的自我摧残》,包振远、马季凡编《中国历代酷刑实录》,第140…141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9《莫言与〈檀香刑〉》,参见李潘《真不容易》,西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78页。
10转引自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83—284页。
11《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49页。
12《红色:记忆与遗忘——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暴力倾向》,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50页。
1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4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5葛红兵《对“9·11”的叫好声体现出现代化思路中的问题》,见《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春季号,149—150页。
16学者王学泰认为,一千年以来,对于民间和下层社会影响更大的乃是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它仿佛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体现游民的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必然是暴力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说唐》那样的通俗小说,以气力和武艺排定“天下第一条好汉”至第N条好汉,第一条好汉李元霸面对一百八十万军马,打开一条血路,双锤到处,纷纷落马,个个身亡。元霸犹如打苍蝇一样,把隋朝将士打得尸山血海。这种对暴力的张扬,对民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且是负面大于正面。有人说,三教(儒、释、道)之外,还有一教,这就是“小说教”(钱大昕语),从影响面来看,的确不错。“小说教”与“三教”倡导非暴力不同,它鼓吹暴力至上,可以凭借它解决一切问题。参见王学泰《关于“暴民”问题的几点思考》,《东方文化》,2002年第3期。
17霍桑《古屋杂忆》,见《蜉蝣:人生的一个象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0—21页。
18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68页。
19《酷刑:人类的自我摧残》,见包振远、马季凡编《中国历代酷刑实录》,第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20《酷刑:人类的自我摧残》,见包振远、马季凡编《中国历代酷刑实录》,第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21《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98页。
22《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99页。
23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7页。
24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7页。
25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7页。
26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
27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6页。
28勒内·吉拉尔《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85页。
29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379页。
30张鸣《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见《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39页。
31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0页。
32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1页。
33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10页。
34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1页。
35张鸣《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45页。
36《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76页。
37泰戈尔《吉檀迦利·59》,《泰戈尔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5页。
38泰戈尔《游思集·11》,《泰戈尔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2页。
39朱大可《“色语”的书写时代》,见《东方杂志》2003年11期。
40见《我们选择的前途——二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全球公众推荐的文字》(上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