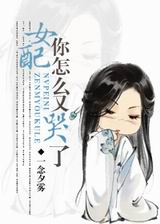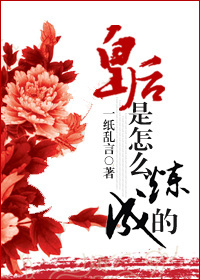妻子是什么-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足迹”,要离开“母亲的足迹”,要变得更富有攻击性,要变得减少攻击性,如果想要成功就得拒绝结婚生子,最后,也可以把这些都不当回事,而是把妻子当作一项事业。
未被讨论的是已经确立的妻子结构。未说出的是妻子并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被迷恋的对象。书店里充斥着大量的与妻子有关的建议。我们被真实和虚构的有关妻子的故事所约束着。不管她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总是忍不住相信比较悲惨的那个版本。然而妻子在女性自我身份上存在的这一难题却很少被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并不会令我们太过感到惊奇。妻子经常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从来都不是主角。
真空渐渐被填满了。妻性鸿沟将不再存在。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政治议程、公共政策、还有利用妻子的含义实施阴险控制的商业力量都在向其中渗透。除了政治上的变化,妻子的角色继续被用做一种女性控制机制。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把妻子置于丈夫的束缚之下的事实曾经被掩盖起来,今天这种束缚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同样,妻子的意义影响的并不仅仅是结了婚的女人。对于14岁的少女和41岁的离婚女人它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涵义。因为它影响到对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一个女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妻性鸿沟是一个概括了的说法,但它非常重要,影响到女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如诗人吉尔·比尔拉思克(Jill Bialosky)在《家里的母狗》(The Bitch in the House)里的一篇文章所述说的那样:“我想过结婚,但我意识到现在我永远不想成为一个‘妻子’。”佩吉·奥瑞斯坦(Peggy Orenstein)在《变迁》(Flux)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结论,奥瑞斯坦写到,“在她结婚的时候,她坚决反对成为‘妻子’”,但是她还是知道她轻易地“陷到了这个角色当中,尤其是它看起来——至少是在短期内对我有利的时候”。在她结婚后的第一年里,她遵循着旧式的丈夫养家口的生活模式,用的方式却非常现代:她把自己的收入看做是属于她个人的,把丈夫的收入当作两个人分享的。
在21世纪,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就像她们曾经想嫁的男人们那样。然而她们依然被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放弃了的女性生活图式的巨大的牵引力所影响着。奥普拉·温弗瑞在她即将结婚的时候说自己将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将会“像一个妻子那样行事”,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今晚秀》(The Tonight Show)中,在观众们看来她说的要像个妻子那样做事肯定指的不是像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或是一个宇航员,再或者是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她说的应该是认真地打扫起居室,做美味的午餐,准备果冻沙拉带去聚会。
旧的图式的残留继续对那些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保护”这个词的女人们发生着作用。研究揭示,年轻女人们期待她们的丈夫能够承担养家口的主要义务,即便是妻子在外工作。另外一份报告指出,有75%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相信她们未来丈夫的工作将会处于优先地位,而女人比男人容易为了配偶的工作而重新调整自己的选择。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11)
当代女性主义把妻子放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一点都不令人惊奇。1998年6月份的《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题目叫“女性主义死了吗?”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把女性主义的运动做了一个编年史的梳理,然后得出结论,认为女性主义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世纪逐渐“陷入愚蠢”。很明显,它依据的是流行文化中对女人们的描述,把电视里那么没头没脑的角色阿莉·麦克白(Ally Mcbeal)与《玛丽泰勒摩尔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中那个头脑冷静的单身女人玛丽·里查德(Mary Richard)做对比。
因为破坏了百年来的女权运动,去谴责阿莉·麦克白的创造者大卫·E·凯利(David EKelley)自然是一件荒谬的事。我们仅仅需要看一下《时代》杂志的封面。它描述了女权主义领导人苏珊·B·安东尼,贝蒂·弗里丹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与单身的阿莉一样都不是妻子。19世纪的妇女参政论者安东尼从来都没有结婚。“我从来都不认为我能放弃自由去成为一个男人的管家婆。”她曾经这样说道。弗里丹曾经是一个妻子,却命运悲惨。她在1969年离婚。这之后,她宣称她丈夫打败了她。在她的《生命如此漫长》(Life So Far)中,她承认她很“惭愧”,因为她曾经否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母亲,我曾经和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们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对女权主义发生怀疑的许多运动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可以发现问题出在妻性鸿沟自身。因为女人们没有意识到女权主义所许诺的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许多争论,而女权主义自身也无法逃避被指责的命运。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引向女性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成为妻子——这一问题被现代许多有影响的女权主义者所忽视。这个将会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沙场,在这里妻子的复杂意义被用各种方式重新定义,其中有些说法试图威胁我们回到女人的权力无法被得到确认的那个旧时代。这并不令人吃惊。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会对妻子重新改造以适应自己的目的。我们这个时代也并无不同。当我们冒险进入由于妻性鸿沟而形成的特殊领域后会发现这一事实更加明显,这个离奇出现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美丽的、商业化的、被麻痹了的新娘,她正在等待着神奇的变化发生。
第二部第二部分白色梦幻(1)
那么这围绕着新娘产生的空洞的喧嚣究竟是来自何处呢?当只有为数不多的女人在嫁为人妇的时候,身穿白色缎子的结婚礼服忙着切蛋糕的新娘却似乎无处不在——这是广告商营造出来的一个迷人的骗局,他们给婚礼蒙上不无色情意味的暗示,然后再把观众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一个新兴的而且在不断扩展的婚礼产业已经形成,婚姻似乎变得更为诱人了,婚姻的意义也似乎更加丰富了。
婚礼产业是可以激发女性成为妻子的愿望,但这个产业的出现也让妻子的意义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结婚狂”是对妻性鸿沟的直接回应,也是填补真空的一种资本化的方式。现代新娘就像是神话传说里的纯洁的仙女,传播希望、纯洁和原初的美好愿望。在市场中,新娘身份只是很短暂的存在,而这一身份更多传达的是其吸引力:与墨守成规的日常生活相比,她短达一天的存在注定她是永远新鲜的。做一个一日新娘,而不是成为一个终身的妻子,这是那些市场的操纵者们奉献给女性的最后的神话,这也是一个试图使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虚构。罗宾·沃德(Robin Ward)是爱丝婷劳德(Estee Lauder)化妆品集团的品牌主管,1998年她曾经在《财富》(Fortune)杂志上这样解释新娘这一形象的功效:“当你想到新娘这一形象的时候,她是永恒的,她在任何女人的生活中都是一种积极因素,对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女人都是这样。无论是现在还是这之前的30年情况都是这样。”
新娘作为一种消费促进剂是如此有效,以致于带有新娘徽章的女人们和各种商品放在一起促销,有些商品其实和婚礼根本就没有直接关系。新娘于是出现在各种广告中:啤酒、谷类食品、冰激凌、可乐、冷却器、人寿保险、香烟、服装、手机,甚至是加拿大的唐人街都用新娘来做广告。作为广告中的焦点,新娘是一个简单自然的符号:她是任何一个场面中的明星,是观众永不可能忽视的精灵,是一幅山水画中最美丽的那道风景,是女性的最为原始的表征。
新娘形象给广告商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叙述模式,给他们一个再一次重复哪一种女人适合做妻子的机会,这一点在一个啤酒广告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新娘把她的头浸在水里为的是给她的新婚丈夫取回那瓶啤酒。而在一张香烟广告招贴中,则暗示年轻的新娘正在努力寻找比她大很多岁的新郎到底把钱放在了哪里。
绝大多数以突出新娘为特色的广告是以女人作为目标受众的。许多女人在成为妻子的时候,内心所怀的感情其实相当复杂。新娘固然是一个短暂的角色,却会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这一重大的变化,她必然会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有一些广告对女性的这种感受有所表现。在一个电视广告画面中,新娘和新郎所处的场景是一个祭坛。新娘正被自己的父亲交给新郎,她的目光注视着墙上的“出口”标志。这时候,画外音响起了:“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决定。有了凯洛格这种营养丰富的食品,你不再需要去做什么决定了。它可靠而有营养。”最后,新娘说话了。“我不知道”,她这样说道。这个回应很显然指向的是新郎,而不是什么凯洛格牌子的食品。
很多时候新娘都是站在一个孤立的背景中,暗示着理想的婚礼场面不过是女性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按照广告的观点来看,这也是有用的。新娘独自一人,看不到新郎身居何处,更有助于表现出一种完美的理想境界——那就是对混乱不堪、错综复杂、平淡无奇的现实婚姻的逃离。2001年哈根达斯的广告招贴上画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是自鸣得意的新娘,她独自一人,正悠然地用勺子盛着冰激凌往嘴里送去。“没有我他们也一样能开始。”这是印在广告上的宣传语。这样一个调子是很吸引人的,因为它把新娘诱人的吸引力和为新郎提供的味道甘美的奶油制品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广告对现代婚姻中浪漫迷人的那一面做了一个很生动的表现——那就是夫妻间不但可以亲密无间,同时也可以完全的自我放任。
作为广告形象,现代新娘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她激起了深刻的反响,她所引起的反作用力超出了市场本身可以计算的限度。她就像她被比喻成的生奶油那样美味。同样,新娘的新角色是作为一个女推销员,这对于她的传统角色而言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因为无论旧角色还是新角色,她究其根本都是被包装了的货物。“Bridal”一词是从古英语中的“ brideale”中发展而来的,或者是“婚礼的宴席(Wedding Feast)”(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和“缰绳”的联系,“缰绳”一向是由“马夫”控制的)。在18世纪的英格兰,吞吃新娘的观念被发展到了很极端的地步,参加婚礼的宾客撕扯新娘的衣服,因为他们相信她的衣服具有神秘的特质。两个世纪过去了,消费新娘的观念被婚礼上的蛋糕这一形式继承了下来,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一脉相承。社会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维瑟(Margaret Visser)指出:“蛋糕高高地耸立在那里,洁白,古老,装饰美丽,呈金字塔状,仿若带着面纱的新娘自己,主导着事件的进程;蛋糕是新娘的另外一种呈现方式,切开蛋糕的仪式是对新娘经过甬道的仪式的一个戏剧化表现。”烹饪作家杰弗瑞·斯坦格特恩(Jeffrey Steingarten)说的话更是直率:“现代婚礼上的蛋糕,就是你吃到嘴里的新娘。”
第二部第二部分白色梦幻(2)
新娘所具有的这种可以食用的特点在大众市场上更是被充分表现。我们已经熟记新娘是任何一场盛会上的明星,但是我们还是被一次一次地告知这一道理。很显然,一个以婚礼结尾的故事拥有的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结尾。谁会不喜欢一个快乐的结尾呢?它是生活中洁净优雅、整齐有序、容易被人接受、令人振奋的最后一幕。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了对新娘的快乐生活的新的、不再那么正统的介绍。
这一方式将身着蕾丝裙子的新娘放在了一场被人窥视的秀场的中心。当婚姻自身成了一场混乱,像一艘失去了压舱物的船那样飘摇不定的时候,对婚礼最准确的定位也许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宣泄了。在2001年9月的一次采访中,拉里·金(Larry King)问奥普拉·温弗瑞为什么不结婚,这个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女性心理的女人非常简洁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美国人并不在意我是否拥有幸福的婚姻。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婚礼……他们想放飞鸽子。他们想看到一袭漂亮的婚纱……”
![[剑三]娘子是个技术帝怎么破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0/5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