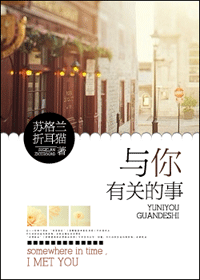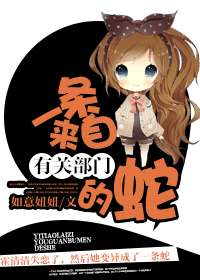有关品质-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旁有买饼家,蒜齑大酢,从耳三升饮之,病当自去”。结果吐出一条蛇来,病也好了。华佗死于公元208年,距张骞带回大蒜三百多年,实际在小铺捣蒜泥食饼已经普及。吃饼而食蒜,我怀疑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食俗。
大蒜列入五荤倒是不足奇,古人认为味重发热之物都易乱性。因为发热,嵇康在他的《养生论》中说,“荤辛害目”,后人因此说蒜能使人视觉模糊,“装蒜”一词由此而来——装糊涂。但辛能散气,热能助火,所有东西都是相辅相成,医家从消谷、理胃的角度,又觉得它“入太阴阳明,通五脏达诸窍”,邪邪得正,所以又“多食不利目,多食则明”,而且“久食令人血清”。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
大蒜的文化问题(2)
…
大蒜调鼎的好处,从西域到中原,被解释成中国文化中的物物相克又物物相融——味味相重不仅更为鲜美而且荤气也在相克相融中减为柔和,如鱼羊为鲜一样的道理。蒜之味重而刺激他物原味,与他物本味相克相融而产生更丰富味觉。其保健功能,一是杀菌,二是去寒湿,以至成为辟邪的象征。对大蒜的赞扬,我见到最肉麻的是元人王桢,他说蒜“味久而不变,可以资生,可以致远,化臭腐为神奇,调鼎俎,代醯酱,携之旅程,则炎风瘴雨不能加,食腊毒不能害,夏月食之解暑气,北方食肉面尤不可无,乃食经之上品,日用之多助者”。他是山东人,以至现在山东人对大蒜的钟情远胜于西域。
…
关于刘欢的疑问(1)
…
3月19日,刘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没见费力拉什么赞助,也没像有些歌手那样刻意做什么推广,票就一下子热销售空。于是大家都在议论:他凭什么就有这样蓬勃的人气——好像是只要他要,就一切都有了——余隆亲自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作伴奏,三宝放下手里的一切活帮他做效果,歌手们是有求都应。一切都像去年他那张专辑——那时候,也像是别人要推着他做这张唱片,尽管唱的都是老歌,大家熟悉的那些影视歌曲一首没有,但唱片好像一出来市场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说法——好像他成了某种象征。他的拥护者好像也不能以年龄层来划分,与周围朋友请教,大家几乎一致承认他的歌“还是好听”,究竟喜欢什么,又说不清楚。
我注意到刘欢是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之后,那时候他已经唱红了好几首歌,但之前却并没能拨动我的神经。注意到他是因为那首片头曲,给我一种极舒展的明亮感觉,因为这感觉,才激起我喜欢姜文在其中的放肆表演。刘欢最初吸引我的还不是他那种与众不同的音色,而是那种拼命也要唱出雄浑的劲头,好像把全身的力都绷成了一张眼看要折断的弓,这全心全意绷着的力也就给人一种非凡的感染力。再注意电视转播中他出场的音乐会,刚开始怎么也觉得他有些声嘶力竭。这声嘶力竭本来是一种拙,但淋漓尽致到真情真意,也就容易触动敏感的情感末梢。再加上这用足了的力把声音拉细成绵绵的柔肠百转,于是就觉得他的歌好像不是那种简单能消化的流行,产生一点喜欢,也产生一点疑问。1993年我们正筹办《爱乐》,李南告诉我,这家伙首先是个古典音乐迷,家里的唱片都是古典音乐,于是对他进一步有好印象,也算是对他的疑问有了第一个答案——深信他的声音来自古典音乐的基础。因为知道他也是个古典音乐迷,自然感到与他有了相近之气。《爱乐》创刊后我们送刊给他,曾想与他有一个对话。后来时间错过,也就作罢。我们所住地方其实也就相隔了一个楼,之后在路上时时与他相遇,见他时时手里托一斤切面,有时还有黄瓜,只拿两根;不需墨镜,见到所有人都是点头报以微笑。想他中午也就是面条加黄瓜,一般的知识分子味道。到楼下理发店理发,小工大工经常说他刚去刚走,也就多几分亲切。在小区里平日见开车的都是他太太,一辆陈旧的“本田”。在停车场,晚上也能碰到他们一家回来停车,在月光下很亲昵地窃窃私语,很亲昵地笑,感觉他们过着平静的日常生活。于是也听说刘欢是个生活在现实之中,又将情感看得很重的人。以我的见识,太太、孩子、家庭都属情感基础,基础缺少情感浓度,他处的情感也一定很稀薄。
由此想到刘欢歌的好处,一是好像什么歌到了他手里,就被加重了情感浓度,而且变成他自己的情感倾诉。大约是他的身体质量在演唱中加重了歌的质量,所以相对那些依靠麦克风轻声曼语、柔顺光滑的演唱,他的歌大都有比较大的幅度,在情感渲染上有较宽的发散力。他又是一个不仅有情感又有激情的人,一点不给自己的声音基础留余地,每一首歌不由自主就都会唱成对自己声音高度的挑战,所以经常在演唱中有“唱背过去”的传闻,由此曾成为被人嘲讽的对象。“唱背过去”意味着音量超过了他的身体质量,在这个人人都准确丈量自己的越来越实际的时代,他的激情“糜烂”也可以成为崇尚节制的人们的批判对象。但激情总是已经丧失激情者的怀恋对象,这种激情也恰恰能使他的声音有了一种金属一样的感觉。
其实在周围歌手中,刘欢的声音条件本来并不突出,他不是“高音之王”,音域比他宽的人也有的是。但他恰恰又能每唱一首歌都能唱出味道。我感觉,他的演唱其实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能超越一般歌手之处,是他在意识到人声是最丰富的乐器之后,能有意识地在每一首歌里寻找声音表现的丰富性,使演唱成为音色变化的表演,变为一种声音丰富性展示的技术。这又是古典音乐给他的好处。在古典音乐中,早期阉人歌手的演唱是最展示原始声音的丰富性,之后在宗教清唱剧与弥撒曲中的宣叙调与歌剧中的咏叹调赋予声音的抒情性。刘欢是从抒情性出发来寻找声音的丰富性。这是为什么他去年推出上世纪60年代老歌翻唱的重要原因,一首《怀念战友》堪称他成功调动自己声音魅力的经典。而《映山红》用弦乐五重奏伴奏,弦乐层次的丰富性成为他声音抒情丰富性的调色板。要是仔细分析,刘欢真正吸引我们的是他的情感发散能力,而其魅力就在于对他声音抒情能力的不断精细挖掘。他的歌中,我以为最具魅力的除了《怀念战友》,就是《弯弯的月亮》与《昨天下了一场雨》,深厚多情的抒情中达到了对音色的精致控制,产生的婉转令人回味。我始终认为,在一种重量追求之后对轻的表达才是最美妙的——比如当马勒的沉重喘息与瓦格纳的强烈冲突之后所表现森林中的喃喃细语,比如干脆以室内乐的单纯来演绎这两位的大作品。当情感浓度与强度转化为声音的倾诉时,也就最容易牵动我们抒情感应的神经。刘欢的毛病是由此过多追求演唱的铺陈,他喜欢管弦乐队那种宏大的效果,但我听管弦乐伴奏下他的效果却并不好——其声音因为达不到帕瓦罗蒂那样的强度而常常掩盖在汹涌澎湃的管弦乐高潮中。像弦乐五重奏这样的室内乐可能更适合他的抒情调度。
…
关于刘欢的疑问(2)
…
刘欢的歌在这个时代中不能算是一种时髦,他是相对那种轻薄与单薄的反抗,但时髦往往必须轻薄、单薄地轻装前行。所以有说法——刘欢的歌迷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刘欢是在为怀旧和对情感的追忆而歌唱。也许,被卡通哺育出来的年轻一代对质量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他们往往认为,快感都在轻佻的游戏追逐之中,负担都是人为悲剧的前提。但没有痛苦基础的快感毕竟只会是在湛蓝天空中飘飞的美丽风筝,能凝结起来的黏稠情感才能在深层上给人以感动。当然,轻松倜傥也能构成质量,但只要大多数人都无法脱离情感纠缠,刘欢的歌就能以一种理想的情感境界,给情感稀缺中的大家以抚慰,他就好比是一根琴弦。
…
非洲的童年(1)
…
二十多年前,在读到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之后,我读到一本好像是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译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童话》。对童话的钟情也许因为每人的童年都最稚嫩也最易在梦中被咀嚼。这本童话中的动物故事要低级于人的故事,搜集的要低级于翻译的。而篇首故事也许因为那种蔚蓝色的感伤,竟成了我珍贵记忆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关于月亮、太阳与星星的故事——太阳是勇士,月亮是美女,它们生下许多孩子都是女孩,就是满天阴柔的星星。悲剧是因为勇士后来越来越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他就不再疼爱孩子们,让她们变得瘦骨伶仃。月亮与她的孩子们因此而哀伤,她们出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等勇士醒悟去追寻时候,与她们永远在追寻的轮回之中。他们再也碰不到一起,再相爱也只能天各一方。
二十多年后,等真正踏上非洲大地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竟是这个在心里蕴积了许久的关于爱的絮语。到非洲的第一感觉,是关于近与远的——天是低的、云是近的,那种云的晶亮好像就悬浮在你的头顶,而树与树之间却是远的。那都是些我梦幻中的树——它们在透明的空间里拼命舒展着每一分枝干,使一个比一个丰硕的树冠沾满太阳银色的水分。在越走越近的白得令人恐惧的云之后,它们一棵一棵,在广阔的草原的摇曳之中,那么孤独地压在白象般的群山之下,充盈着那样的生命水分,含蓄着自己胀疼的力,一棵又一棵地遥遥相望。
所谓味道,也就是一种自作多情的咀嚼吧。由此觉得到南非的十多天好像只有两天是最难忘的——第一天在一个叫Makalali的营地,第二天的营地则叫Sabisabi。它们在一堆堆云的覆盖、一棵棵树的护卫、一片又一片锯齿般在苦艾的风中舞动的绿草缝隙之中。Makalali营地比Sabisabi营地更具野性魅力——一个营地十多间独立的茅草屋,每间屋顶都弯着一对牛角,屋前屋后都有特立而风摇不动的树。屋朝山而立,陈旧而笨重的木板屏风,中间一门闩,吱扭沉闷地响。门前有廊,沙发两只,让满山空翠染成青苔色。推开侧门,淋浴喷头在露天,面对整个山野。屋畔有茅亭,亭中有巨大的垫子与滚筒般夸张的枕,亭下流水潺潺;两人在亭中剧烈运动,垫子会自然分成两半。作为私人承包的野生动物园,其浪漫表面是下午四点到七点在阳光变得温柔后坐着敞篷的“陆虎”吉普车去四处搜寻狮子、猎豹与大象。动物们散在草浪之中,欧洲贵族们残存的乐趣其实是在寻找本身,而非是真正与动物们频繁亲密接触——整整一小时你可能都在寻觅的期待中,有味道的其实是你身前身后那些被夕阳燃烧的树与变得色彩饱和的云。那些树在夕照中更倔强地伸展着那种在孤独中凝聚的力,而那些在夕照中像滚雪球般越滚越丰腴的云也在越来越膨胀着自身的力。原始的生命永远那样刺目般耀亮,刻在我心里最刺目的形象是那亮得不能再亮的云堆里闪电那种与云挣扎后剧烈变形的曲线。血红色闪电的亮与云堆积着的亮强烈对比,两种亮度与两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彼此撕裂。
那个难忘的夜晚,在那样遥远的地方,忽然就对时空有了一种全新的启蒙。当树与云从剪影变成温柔的一片,流动在你周围后,星星好像瞬间从你眼中跳跃出来,与它之间再没有任何阻隔。童年枕着青草面对整个星空的记忆完整地全浮现在一个空间中,天地一下子从广袤变成全是你私有的。狮子的吼声闷闷的,好像就在不远的地方,是那样原始有力的做爱声音。土狼也在那里求偶,声音那样猥琐。但庄严者与猥琐者就同样在一个空间里享有同样的欢乐。我们在制高点喝啤酒,回营地的路上,素质极好的导游林达提议吉普车熄火、关灯,大家突然就整个掉进童年的夜色之中,周围在瞬间的静寂之后,各种声音一下子都浮现出来,构成自然的交响——无数生命在蓬勃生长中发出各自最美丽的声音,交杂成最美丽而丰富的和声。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它们就在你周围,你自然地觉得自私的基因正一点点融化,正变成这种庄严交响的一部分。你在一个庄严的穹隆之下,你在这种交响合唱中,完全是被宗教合唱抚摸的那种庄严感。
那天晚上,沐浴在漫天星光之下,一身清净一身轻盈。屋内偌大一顶蚊帐占据了整个屋子,山风吹动灯光下蚊帐飘曳。推门独自坐在廊下,整个山林荒野好像都向你聚拢过来与你亲近,风凉而透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