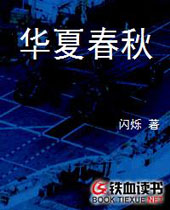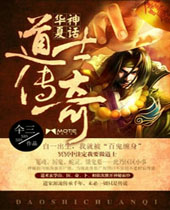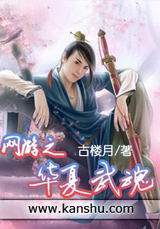龙兴华夏-第3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在京王公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太后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自此,宫里****有隆重的庆祝活动,直到十月十七日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庆典的高潮。这天,宁寿门外至皇极门外设慈禧太后皇太后仪驾。辰刻,慈禧太后御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至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至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斗坛等处拈香行礼毕,还乐寿堂。巳初,慈禧太后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同治皇帝于宁寿门中门入,诣慈禧太后前跪进表文,宫殿监侍一员跪接表文,安于宝座东旁黄案上。同治皇帝步行至宁寿门槛外拜褥上立,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随后,接受皇后、慧妃、瑜妃、各公主、福晋等参拜。礼毕,慈禧太后还乐寿堂,升宝座,同治皇帝诣慈禧太后前跪递如意毕,皇后率慧妃、瑜妃等诣慈禧太后前跪递如意毕。慈禧太后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至阅是楼院内降舆,同治皇帝率皇后、慧妃、瑜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戏毕,同治皇帝率皇后、慧妃、瑜妃跪送,慈禧太后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还乐寿堂。
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怀着不无激动的感恩的心情写道:“济济焉,盛典哉!”
当然,对于这次的万寿庆典,绝大多数的清流士子们对这当中的巨大花费颇为腹诽。直到后世,很多人还专门详细考证了这当中的花费,认为靡费过甚。
根据史家言之凿凿的考证,当时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当中的花费,主要有三项:
一、备办太后专用器物、修缮等情形:
龙袍、龙褂、氅衣、衬衣,各色蟒缎、丝绸等面料。共耗资二十三万二千余两银子。
加徽号所用玉册、玉宝、册文、宝文,金箱、金印等,合银三十八万六千两。
金辇一乘,耗银七万六千九百一十三两。
各式暖轿、亮轿、漆车灯,共耗银七万八千九百余两。
彩绸工费、津贴等用银十四万四千一百五十两,彩绸用银八十六万六千六百一十两。
皇城根车站至“天地一家春”小铁路修缮工程(即采石场、木厂通往工地的工程小铁路,“天地一家春”完工后,改成了宫内到圆明园的客运铁路),铁路花费三万二千两,机车、车厢、花车花费九万一千两。
紫禁城等处灯只需银二十万两。
重修“天地一家春”,耗银一百余万两。是为开支当中最大的一项。
二、修葺街面、点设景物情形:
庆典期间,凡慈禧太后由颐和园进宫所经过的道路两旁,街道铺面要修葺一新,并分段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
龙棚、龙楼、经棚,每段用黄缎龙旗一面,祝嘏牌一对,上书“某处某官恭祝万寿无疆”字样。每段安设鲜花数盆,派官员、茶役、士兵三十八人照料,僧众、乐师二十九人。共六十四段,每段需银四万两,共需银二百四十万两。
三、筵宴、演戏、仪仗情形:
庆典期内,照例要赐群臣宴,单筵宴一项,耗银二十三万两;乐师等所用各项约用七万两。唱戏所用各项耗银五十二万余两。
庆典期间,慈禧太后乘“金辇”自“天地一家春”还宫,或从宫中前往中南海、颐和园、天地一家春及举行仪式、筵宴时,需大量请辇校尉、太监及浩浩荡荡的仪仗队。请辇校尉达七百九十八名,苏拉一千六百二十八名,执役校尉一千三百六十二名。上述人等衣饰等项耗银约十五万两,黄金三百六十四两。置办赏赐物品等约三十多万两。
而如此巨额的花费,据记载并未从国库当中调拨,因而其来源问题,后世的史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筹办这次“万寿庆典”所需经费,一部分应该是由“部库提拨”,也就是还是出自于户部,也就是国库,只不过换了名目。从部库提拨之款,来源可能有两项,一为从“边防经费”中提用一百万两,再为“铁路经费”中“腾挪”二百万两。另一部分应该是由“京外统筹”,所谓的京外统筹,也就是京内外臣工摊派的报效银两,达二百余万两。以上只是有据可查的现银,其他帐外的巧取豪夺,无法统计。据“历史学家”们估计,这场庆典共耗银一千多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岁入的六分之一,足以再装备一支“大清帝国海军”!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次庆典的经费来源,并不是出自国库。有清一代,对于国库收入的记载,最为详尽,当时的国家收支,大体上是平衡的,每年的结余都不多,到了年底,国库若能有二百万两银子左右的结余,便已经是好年景了。如果这场庆典真的花费了一千万两银子的话,是国库万万所无法承受的。而且从户部的收支档案记载来看,并无关于庆典花费的任何记录,也就是说,这些花费,并不是出自于国库。也不可能出自于国库。而前论者所说的什么“边防经费”和“铁路经费”,并无此类开支项目,只是别有用心者的捕风捉影和虚妄之谈。
第三百九十七章借着园工修铁路
当时正值1874年年末,虽然大清帝国成功的击退了日本对台湾的入侵,但一向为****所轻的东海小国日本竟然仅凭着几艘铁甲兵舰和几千使用西方武器的部队,竟敢窥伺****疆土,对中国朝野的刺激可谓极大。而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大清帝国很快开始了第一次海防大筹议,而之前一直为国内保守顽固势力所阻挠的铁路、电报、造船、采矿等一系列对********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业,也都得以借机兴办起来。
这些事业的兴办,从时间上说,正是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之后,何来从什么“边防经费”、“铁路经费”中“提用”、“腾挪”之说?
实际的情况则是,因为台湾之役刚刚结束,军费开支浩大,为了节省开支起见,慈禧太后下令庆典尽量从简,是以在1874年的万寿庆典中,诸如“点景”、“修葺街面”等项,全都取消了,除修“天地一家春”耗银一百余万两为大宗之外,整个庆典的花费,据部分学者查阅清宫内务府档案详细考证,当在三百万两白银左右。
而这三百万两白银的来源,主要出自“京外统筹”,即各地官员及商民的“报效”。
根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各省“报效”的数额如下:
直隶:20万两。
江苏:20万两。
江西:10万两。
安徽:20万两。
广东:20万两。
广西:20万两。
福建:10万两。
浙江:20万两。
四川:40万两。
湖北:20万两。
湖南:20万两。
云南:5万两。
贵州:5万两。
河南:5万两。
山东:5万两。
山西:10万两。
陕西:5万两。
甘肃:5万两。
东北各省将军:20万两。
此外还有:
台湾商民感恩报效银:4万两。
琉球王尚泰进献银:6万两。
雪域卫藏****班禅进献银:10万两。
康藏众土司头人进献银合计:20万两。
山西殷商乔家(乔世庸)报效银:10万两。
湖州殷商席家(席正甫)报效银:10万两。
云南殷商王家(王炽)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陈家(陈廷轩)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潘家(潘仕成)报效银:10万两。
海外殷商卢家(卢仲恒)报效银:10万两。
以上合计:380万两。
这些“统筹”和“报效”,才是慈禧太后1874年万寿庆典的真正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为左宗棠倚重并向朝廷举荐表彰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没有给这一次的太后生日庆典出一分钱。
看到这长长的帐单,有人会问:花费这么多金钱,举办这样一场铺张浪费的庆典,有必要么?把这些钱省下来,用于救济百姓,或者兴办实业,岂不是更好?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日本刚刚入侵台湾未能得手之际就大搞特搞庆典,那么清王朝的覆灭,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也是独裁王朝不能逃避的轮回。
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很多历史学家都这样认为,慈禧搞万寿庆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显示大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光环,此前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将近200多年,到19世纪下半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尽管有像曾国藩、文祥、李鸿章这样的“中兴名臣”来维持,也是衰落之象尽显。
慈禧在中日甲戌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搞生日庆典,不光是为了满足帝后们的文化娱乐需要。
在中国的社会中,逢旬寿时(即满10年的生日)往往比平常的来得隆重。即便是作为普通中国人而言,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此论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之过往恰恰也是属于情理之中。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操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生日庆典活动是人之常情,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而这样一场庆典,不但可以向国人显示国家的富足,也可向外国显示清王朝的强盛。
指责历史上的慈禧太后铺张浪费,为了面子和形象,没把银子花在了老百姓身上,那么后世的兴办奥运会和诸多的这个“会”那个“节”,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却又令无数“爱国青年”为之无比狂热兴奋激动自豪呢?
在清王朝最后统治中国的近一百年中,中国可谓是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这个在世人眼中腐朽没落的王朝中,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了社会和国家的危机,但是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时,他们没有反对,而是明白事实上受益的,并不只是高层人士,底层的民众也是受益者。
由于庆典的经费来源于“京外统筹”,并没有给国库增加额外的负担,而和庆典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后,使各地相关的手工匠人都有了额外的工作和收入。而“天地一家春”等园工的兴建,不但促成了铁路这一新兴事物在中国生根,还给北京郊外大量的穷苦旗民找到了工作,“赖以为食者十余万人”,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底层的民众是从中得到了不小的收益的。
后人评价说,仅就促成发展铁路一项,便可以说是这场庆典的最大意义所在!
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农历),太后万寿第二日。
张佩纶坐在张灯结彩的小火轮车车厢内,打量着周围,饶是他平日里镇定自持,轻易不假于颜色,此时此刻,他的脸上也和诸多一同乘车的官员们一样,写满了惊愕。
今天是他们这些言官们为皇太后祝寿的日子。
但是令言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前往“天地一家春”贺寿并接受赐宴时,他们竟然看到了令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东西!
火车!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火车这种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万分痛恨的事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了京城!
而今天要他们乘火车前往圆明园“天地一家春”贺寿,张佩纶感觉,似乎是皇太后有意要给他们这些言官一个提醒儿!
或者说是警告。
甚至可以说是折辱。
现在,不光是张佩纶有这样的感觉,大多数上了车的清流言官们,脸上都有一丝愤然之色。
可他们还偏偏不敢不坐。
君赐不可违!这个道理,他们这些个饱读圣贤书的,当然再清楚不过了。
此时的宝廷和黄体芳,正气乎乎的坐在那里,小声的交谈着。
“回头我便上折子参他!这一次我定要参他!”黄体芳的声音远远的传来,虽然不甚大,但张佩纶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他当然知道,黄体芳打算参谁了。
“听闻皇太后允准外国公使参加庆典呢。”宝廷说道,“太后御前,也要有不跪之臣了。”
“那我今儿个便上折子!绝不能让夷人玷辱我华夏盛典!”黄体芳说道。
张佩纶听了黄体芳的愤愤之言,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有心想要劝说一番,但碍于好友情面,思忖再三,还是决定算了。
进入十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然很冷,张佩纶现在,只想快快的回家,远离这个让他感到不开心的地方。
厚厚的衣服,在冬天的讯号里漠然的臃肿。张佩纶坐在车厢里,随手掏出一本书消磨时间,几个太监看到他的动作,窃窃偷笑不已。
远处升起了淡淡的雾气,黑色而朦胧的山峦,寂静的矗立在铁轨的两侧,以一种睥睨众生的傲然俯览这匆匆穿过的小小长虫。北京郊外的天空依旧灰沉沉的,敞开的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