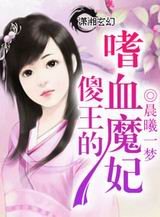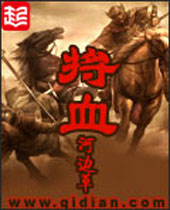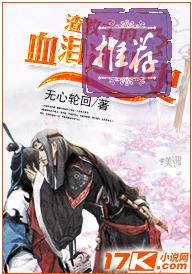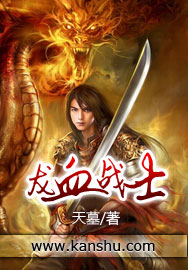晋颜血-第3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去罢,孤要和陛下说些话。”
任皇后瞥了眼那薄纱掩映下的撩人春色,就寒着俏面,略一挥手。
“这”
众女看了看李雄,李雄也一副兴致被败坏的样子,摆了摆手:“下去。”
“诺!”
众女施礼离去。
李雄这才不满道:“当今国家安定,风调雨顺,民众安居乐业,朕忙里抽闲,乐呵乐呵,又怎么了?”
李雄对任皇后还是有些尊敬的,这不仅仅与家世有关,如果与任皇后不和,那么国中必生动荡,同时这也与任皇后的品行有关,任氏素来以贤后自居,也严格要求自己,在国中人人敬重。
但是夫妻之情如果只剩下了相敬如宾,而且任后又无所出,现代婚姻尚有七年之痒,更何况任后嫁给李雄,已经有了足足十年呢?
在李雄眼里,任后不解风情,永远都穿着中规中矩,色泽灰暗,把身体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衣物,每天都对自己说着扫兴的话,还干涉自己的生活。
如今李雄对任后,便是满腔的厌恶和不满。
任后施礼道:“妾乃一妇人,岂敢指责陛下,不过陛下以为,天下就真的太平了么?“
”呵“
李雄呵的一笑:”莫非你当朕不知外间之事?羯胡受挫,刘曜大败,晋主两废,而这一切,皆因明国崛起,可这和朕又有何干?巴蜀据山川之险,恰可观中原风云激荡。“
”唉“
任后叹了口气,幽幽道:”孟子曾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莫非陛下忘了蜀汉是如何亡的,怕当初刘禅亦是如此作想。“
”哼!“
李雄面色一变,不耐的哼道:”朕不是那安乐公,杨彦之也不是晋文。“
任后道:”明国蒸蒸日上,日前已占了襄阳,他日兵分两路,一路西进入汉中,另一路南下由白帝城入蜀,请问陛下如何抵挡?
连石勒、刘曜都相继败于明军之手,莫非陛下以为我成国之卒能稳胜刘石?
陛下言自己不是安乐公,可蜀汉至国灭之前,从未停过北伐,武候有六出歧山,姜维有九伐中原,而陛下有什么?请陛下恕妾直言,我大成,已有十年未动刀兵,陛下不可轻怠。“
“那依你之见,朕该如何?”
李雄心中不喜,沉声问道。
任后道:“陛下应选贤任能,操演兵马,先平南中后患,再依山川之险,拒北方大敌,方可为长久之计。”
李雄问道:“如何选贤任能,莫非朝堂诸公还不够贤?”
任后是地道的蜀人,受气候滋养,水灵灵,柔嫩嫩,只可惜李雄觉得任后不够大胆开放,床榻上的风情不足,很快就对她没了兴趣,毕竟作为皇帝,身边美女环绕,任后再美,也会被淹没在花海当中。
不过任后一口软糯的地道蜀音,倒是颇为悦耳。
当时的蜀中口音,并不是现代人听到的川音,现代川音源自于俚僚南蛮,是南中俚僚趁着三国时期,巴蜀丁口锐减陆续北迁,逐渐潜移默化的结果。
这时,任后便操着一口软语,劝道:“陛下少花时间和那些女子、道人相处,多和公卿宗室往来,另妾听说,陛下有意以李班为嗣,不知传言是否属实?“
任后口中的道人,自然是蜀中天师道系师张昭成,那些女人,是他的妃嫔,这已经让李雄心中隐有怒火滋生,再提及立太子,李雄更是忍无可忍,低斥道:“够了,妇人做好该做之事,何必妄议朝政?”
第568章 合纵联横()
李班是李雄亡兄李荡之子,三十七岁,为人谦虚,广纳谏言,礼贤下士,深受李雄喜爱,欲立为太子。
但问题是,李雄自己有十子,故没有弃子立侄的道理,于是群臣纷纷反对。
李雄辩道:“朕起兵之初,举手捍头,本不希帝王之业也,值天下丧乱,晋氏播荡,群情义举,志济涂炭,而诸君遂见推逼,处王公之上,本之基业,功由先帝、吾兄嫡统,丕祚所归,恢懿明睿,殆天报命,大事垂克,薨于戎战。
班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
李雄叔父李骧与司徒王达谏曰:“先王树冢嫡者,所以防篡夺之萌,不可不慎,吴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专诸之祸,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变,犹子之言,岂若子也?深愿陛下思之。”
其实李雄不是不愿立自己的子嗣为太子,他的父兄战死至今,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要说有存有多少感情,恐怕要打个问号,关键是李雄诸子不成器,要么庸碌无为,要么贪吝暴戾,无人能继他衣钵。
立李班,也是不知己而为之,当然了,李雄不可能于人前指责自家子嗣的诸多不是,只能托词于不忘父兄旧情。
更何况立太子,素来是敏感之事,朝臣大多反对立李期为太子,反而使李雄猜忌,激起了李雄的逆反心理,今任后旧事重提,李雄的怒火终于爆发。
“这江山,是朕的江山,传给谁,朕自有主张,可是李镶叫你来说朕?此事莫要再提,退下!”
任后浑身微震,美眸中现出了不敢置信之色,怔怔看着李雄,许久,才摇头道:“外有强敌虎伺,陛下却凭喜好不谏良言,妾怕是不得善终矣!”说着,便提起裙角,掩面而去。
“放肆!”
李雄望着任后的背影,暴怒,还如气恨难平般,狠狠一脚跺在了橇椅上,顿时喀啦一声,硕大的椅子陷了下去。
攻打成国急不得,需要做诸多准备,其中的关键是道路,自古入川,都是走汉中—阳平关—剑阁一线,但是由襄阳到汉中,全程将溯沔水而上,而沔水在东出汉中盆地之后,奔行于秦岭当中,水流湍急,两岸峭壁林立,车马难行,因此从襄阳入蜀,只能下江陵,沿江西进,走陆逊迎战刘备的旧路,由夷陵进军白帝城,扼三峡出口,攻占奉节,取江州,方能打开入川的道路。
此江州并非晋室分荆州而来的江州,而是晋梁州州治所在,后世名重庆。
杨彦揉了揉脑壳子,暂时把这事放下,毕竟洛阳、宛城和襄阳要全力经营,将士们也出征很久了,需要适当的放松一下。
不知不觉中,三个月过去,襄阳的天气日益严寒,杨彦利用这段时间,首先搞清算,以检举揭发的方式,清洗当年迎赵军入城的带路党,涉及到十余家,直系全部斩杀,旁系充作劳改犯,筑路修堤,女子则以蒙眼摸妻的方式,强配给有功将士。
虽然清洗很血腥,但是襄阳大户普遍持欢迎态度,毕竟带路党往往于郡府担当要职,这部分人被清洗掉,大量的职务也空缺出来。
其次是征兵,明军在襄阳,原有步骑五万,在三个月的征兵中,总兵力扩充到了十万,俱是骁勇善战的秦雍流民,如此巨量兵力屯聚于襄阳,不可能瞒过有心人,最为紧张的,还是王敦。
姑孰,采石矶。
采石矶位于姑孰城南,突兀江中,绝壁临空,扼据大江要冲,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是建康的南大门,王敦负手立于采石矶海拨最高的翠螺山上,望着那奔涌的大江,久久不语。
迎面是江心洲,再往西去,便是历阳,本该与姑孰互为倚角,拱卫建康,但历阳已经被明军占了,江北除了广陵,皆属明国所有。
王敦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无力感,还有着难言的悔意。
如果如果当初在石头城
钱凤站在王敦身边,据他了解,沈氏自从迁徒到叶县之后,由兖州刺史傅冲亲自过问,按占田制授田,并按沈充生前的官职,享五品官待遇,可实际上,占田制养不活沈氏近千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家族拆分,以个人名义占田。
作为沈氏的旁系,是持欢迎态度的,毕竟有了自己的产业,吃穿用度不用再从族里支取,受嫡系严格限制,用现代话来说,实现了财务自由,但钱凤不寒而栗。
从表面上看,沈家还是那个沈家,而在根子里,最重要的财权被分割了,维系家族只剩下了血缘与责任,在若干代之后,这份凝聚力还能余下多少影响?
钱凤或许说不出一切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这个根本道理,但他内心隐隐明白的,就如他的庄园,一旦入不敷出,佃客会渐渐逃亡,乃至忠心的部曲也会大部逃散,最后轮到血亲。
杨彦的手段,除了毒辣,他没法形容,突然他又想到杨彦曾试图招揽自己,他这一生,因发小之情,只忠于沈充,如今沈充死了,还是自己作死,实是没有理由去憎恨杨彦,同时他对王敦既谈不上忠心,呆在王敦身边,还有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
而杨彦给他的印象,是待人和气,眼神真诚,相处时没有太大的压力,却又会不自觉的为其魄力和魅力所折服。
‘难怪能于短短几年内,聚起诸多英豪,我若投奔过去,或可更好的照料士居兄的家人’
钱凤心动了,只是背主投敌
他越想越是心里烦乱,却很难下定背弃王敦的决心,恰于此时,又留意到了王敦的神色,于是问道:“丞相可是为江陵担忧?”
“是啊”
王敦点点头道:“由襄阳往江陵,仅四百余里,从沔水可顺流而下,江陵若失,武昌难保,而江陵太守乃邓岳族弟邓宇“
说到这,王敦不说了。
钱凤明白王敦的意思,因着邓岳被义释一事,又自行回了荆襄,等同于背叛了王敦,于情于理,王敦都该安排自己的心腹驻守江陵,但邓氏是荆襄大族,影响力巨大,在这节骨眼上,如果撤换了邓宇,又怕邓宇会直接献江陵给明国,再如果密谋暗害邓宇,邓岳拥兵在外,能不报复么?这才是让王敦为难之处。
钱凤沉吟道:“一动不如一静,依凤猜测,杨彦之于襄阳屯兵,目的恐怕是巴蜀,毕竟羯人还在与鲜卑人开战,他若于此时北攻河北,只怕双方会联起手来,同时明军在攻下了峣关之后,并未一鼓作气攻打长安,恐怕亦是存了坐看关中内乱之意。
而江东朝庭,凤认为杨彦之应于荡平北方之后,方会南下,故于襄阳屯兵多半是剑指巴蜀。
巴蜀本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能取之,明国实力大增,并可出剑阁,取汉中,沿诸葛亮歧山旧道兵临秦州,再与武关两面合攻,刘曜插翼难逃,丞相须早做决断才是。“
王敦的眉头拧的更紧,钱凤的分析有理有据,杨彦攻打成国几成了定局。
”士仪以为寡人该如何?“
王敦问道。
钱凤望着大江,缓缓道:”丞相应与陶侃和解,拥立当今主上,韩信尚有胯下之辱,丞相向陶侃退一步不算什么,不过司马冲不可封为番禺王,可改封别处。“
”嗯“
王敦捋须道:”那老奚狗虽执中枢,但日子并不好过,其诸子亦不争气,想必也有与寡人缓和之意,也罢,寡人先放出风声,看那奚狗如何应对。“
钱凤又道:”其二,应力保巴蜀不落入明国之手,丞相可使人与李雄结盟,说其兵出白帝,与丞相共同防备襄阳之兵,若李雄不识好歹,凤还是那句老话,取巴蜀,抢在明国之前,灭去成国。“
这是钱凤第三次提议出兵巴蜀,以往王敦尚有入主建康的雄心壮志,但随着明军的节节胜利,再有陶侃入都,王敦事实上被排挤了出去,使他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于是点点头道:”士仪代寡人跑一趟成都,如何?“
”诺!“
钱凤拱手应下。
第569章 陶侃立场()
(谢谢好友秋月落飘零的月票)
“哦?”
陶侃虽入主中枢,但其一贯谨慎小心的性格,使之并不过于干涉朝政,主要政事由郑阿春与庾亮、卞壸等朝臣处理,他只把军事抓在手上,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作法,不过对于外界,尤其与明国有关的信息,他还是很上心的。
这时听得其子陶瞻来报,便讶道:“京中竟有流言,那王逆似有承认晋主之意?”
陶瞻拱手道:“阿翁,想必是杨彦之取了襄阳,王逆独木难支,方有重归朝庭之心,儿以为,王逆大势己去,不足与谋,一旦杨彦之攻打江陵,阿翁应即刻兵发姑孰,分一杯羹。“
”诶“
陶侃摆摆手道:”莫非你不见魏蜀吴之故事?若非吴蜀两家联手,安能抗魏数十年之久?“
陶瞻冷冷一笑:”阿翁,联合抗魏数十年那又如何?吴蜀最终不还是被魏国吞并?既然如此,吴蜀何必各怀鬼胎,互相算计,倒不如一方并吞另外一方,壮大自己,独立抗魏,岂不是少了诸多掣肘?
更何况王敦狼子野心,怎甘心蛰伏于阿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