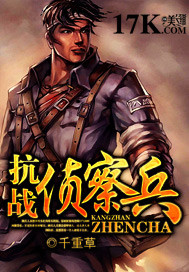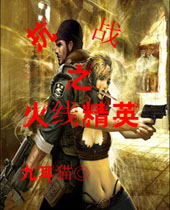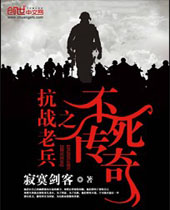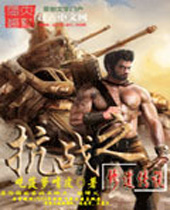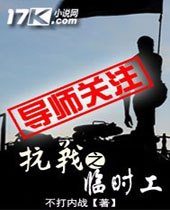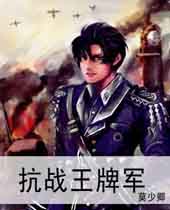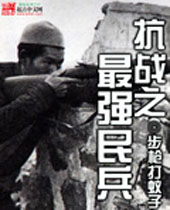湖西抗战走廊-第2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邢田兄弟呀?啥时辰来的?”
那女人已经跑到后墙根,仰着脸,小声地问,话音里透着亲切。
“一会儿再说。”
二嫂说着缩回头去,转过身子,让出空来,示意邢田爬窗子。
邢田明白了刘二嫂的意思,一纵身,头伸进了窗户,转眼,落在了后院。
刘二嫂把窗户小木门关好,放下画着一个胖娃娃骑红鲤鱼的绵纸窗帘,就推王煌铭躺在床上。
没等刘二嫂把被子盖好,院门就传来“嘭嘭嘭”的砸门声。
“来啦来啦。”刘二嫂一叠声地答应,一边给王煌铭掖被角,同时小声地吩咐,“您千万沉住气,当病人,别吭声,鬼子那边,我应付。”
门哗的声,从外面被跺开,一个络腮胡子的小鬼子,跨进屋门,手握着的短枪,抵在刘二嫂的胸口上,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厉声喝起,“说,毛猴子的,有?!”
另一只手,比成一个“八”字,送到二嫂子的鼻子尖,眼珠子瞪成了琉璃球。
“毛猴子?没……见过。。。。。。俺妇道人家。。。。。。出门少,没见。。。。。。”
刘二嫂两手紧紧地抱在胸前,脸怔怔地,吓得苍白,连连摇头。
她毕竟是一个农村妇女,在一个凶神恶煞的鬼子面前,心里再镇静,也避免不了害怕。
刘大伟赶紧上前,点头哈腰,“太君,她个,就知道锅台的妇女,哪见过啥猴子老虎?”
刘大伟转过身子向刘二嫂,“二嫂呀,皇军是好人哩,别害怕,皇军找‘八路’的干活。”
“俺可没扒过人家的路,再说,俺吃饱撑得,扒人家路干啥?”
刘二嫂急急地摇头,她真真切切地害怕了。
“太君,床上有人!”一个头戴鬼子帽,身穿中国衣的男人猛叫。
“什么的干活?!”
络腮胡子一把推开眼前的刘大伟,一步跨到床脚边,短枪抵在王煌铭的脑门上。
“他是俺男人,发病打摆子。”
刘二嫂一下子扑到床沿上,拿袄袖子擦王煌铭的脑袋,“发汗呢。”
她放下袖子,不经意间,把鬼子的短枪,挡开了脑袋。
“二哥,不是叫你外出躲摆子去了,咋回来了?”刘大伟上前看着王煌铭,一叠声地抱怨。
躲摆子,是治疟疾病的一种办法,迷信,因为穷人没钱买药,就是富人也没处买治这病的药,民间传说,打摆子的人,躲到外面去,不见亲人,三五天就好。
现在知道,患疟疾,抵抗力大的,硬抗三五天,不吃药也能好。
一个鬼子,用枪上的刺刀,挑开王煌铭身上的被子。
王煌铭近日来频繁作战,饥饿劳累过度,早已面黄饥瘦,颧骨高尖,胡子拉遢的,真像个病人。
“外面冷……冻得……冻得受不了。”
王煌铭牙打着颤,结结巴巴地回答刘大伟的问话。
“王翻译的,”络腮胡子有些相信,问穿中国衣的男人,“打摆子的,是什么的病?”
“皇军,”被唤作王翻译的汉奸男人,赶忙点头哈腰,“ 太君,打摆子的,就是皇军通常说的发疟疾,传染病的一种。”
“发疟疾?”络腮胡子一听这个名词,连连向后倒退几步。
那个时候,疟疾是最可怕的疾病,人一旦染上,几分钟就会发作一次,一会儿冷得浑身打颤,像掉进冰窖;一会儿像进蒸笼,热得遍地打滚,几次过去,连端碗的劲儿都没有。
武汉保卫战时,日军稻田旅团,就因为军中传染疟疾,丧失战斗力,第一个整建制退出作战序列,所以,侵华的鬼子兵特别害怕这个病。
络腮胡子放下王煌铭,转身满屋子乱瞅,他发现了正冒着烟的鏊子。
一步走上前去,左瞅瞅,右瞧瞧,又抽出军刀,挑开摞成一摞的煎饼。
刘二嫂赶忙走上前,“太君要吃煎饼?俺给你叠。”说着蹲在络腮胡子的眼前,叠起来煎饼。
“太君,这是高粱面,掺上芋头叶子、芋头梗子,合在一块摊的,蒸窝窝,蒸不成个儿。”
刘大伟见刘二嫂的神情,觉得鏊子下面有文章,赶往上前帮腔。
“煎饼,猪食的,哼!”
络腮胡子推开刘大伟,向门口一招手。
一个鬼子,牵一条狼狗走来。
狗嘴里喷出的热气,将地上的芦灰喷溅,升起的芦灰顿时将近前的鬼子熏的打喷嚏。
狼狗耷拉着猩红的舌头,这里闻闻,那里嗅嗅,两个前蹄子,扒得芦灰,满屋子飞扬,鬼子们捂着鼻子眼,往别去查看。
一会儿,狼狗,嗅近了埋枪的灰堆。
两个蹄子交替着扒。
刘二嫂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儿。
刘二嫂急中生出来智慧来,就手,扬扬手里的煎饼,抬头望牵狗的鬼子,“狗儿吃煎饼?”
不等鬼子回答,煎饼扔在了狼狗的鼻尖。
狼狗吓了一跳,退后几步,又伸长脖子,鼻子拱着地上的那个的煎饼,翻来覆去的嗅,最后,抬起狗头,望牵狗的鬼子。
鬼子得了暗示,一勒拴狗的皮带,转到别的地方。
刘大伟长出了一口气。
刘二嫂抬手擦擦额上的细汗。
“开路开路的!”
最后,落腮胡子一扬手,下了离开的命令。
第六节、张韵涵就没这么顺了()
第六节、张韵涵就没这么顺了
李文德在四老虎的攒掇下,一下子抓了狂,狗撵鸡似的追赶着那些伪保长们敲着铜锣满世界抓八路。
张蕴涵用生命掩护过湖干部的安全。
面对张蕴涵大义凌然的牺牲和日伪军的残暴,极怯弱的百姓受到极其强烈的震撼,激情杀敌,加入了抗战的行列。
百姓舍命不舍命救护,一下子显出来
张蕴涵虽也被打散,躲在了一个农户家,但她没有王煌铭、邢田的幸运,这个大命的少女,在更凶的恶鬼面前,再也没了神灵的庇护。
杆子会、红枪会配合着皇军,胜了公安队,一下子露了脸,李文德一等家伙儿,一下子返了阳,像撒欢的叫驴,满湖西地窜,狗撵鸡似的追撵着那些伪保长们,敲着铜锣,满街满巷,喊着抓八路。
按说,四老虎从心里瞧不起李文德,这土财主又贪又笨又没眼力架。可他的手下,死的死,逃的逃,反的反,已经没有了顺手的。
李文德再窝囊,手里却攥着杆子会,有就比没有强,又赶上了这跑场子的事儿,于是捏着鼻子违着心,按着山口的命令,重又封他当了副司令,负责清剿扑捉散逃的八路军。
没想到,土埋到眉毛的李文德,官迷得分不出五和六,脚下安了弹簧,拼着老命的耍官谱,伪保长们,被他逼了一个急,狗撵腚,四处扑八路,弄得个湖西鸡飞狗跳。
张老六是老实人家,在村里户族小,所以胆小怕事,整年价,关着屋门过日子。
眼下,一家人,正就着油灯在喝汤。
喝汤,就是吃饭,冬天天脖子短,过着精细日子的老百姓,就把晚上饭掐了,直到黑晌时候,喝碗稀的汤水,防着睡下了,不再饿醒来。
徐振山,正按着李文德的命令,盘腿坐在人家的炕沿上,劝说着如何的灭八路,已经劝说得嘴角冒白沫了。
——我说爷们啊,这几天,皇军正在湖西,搞着大扫荡,见着“八字头”的,就砍就杀,像是有冲天的大仇,都杀红眼啦。还明说着,谁帮八路,就株连九族,孩芽不剩,咱可别沾这腥手。
“是喽,咱关门,过咱的清静日子。”
张老六放下碗,右手掌抹一下嘴巴,而后,操在棉袄袖笼里。
徐振山呲牙一笑,“还是老六明白事儿,你想想,谁要真帮了八路,到时候,能脱清身吗?你跑得了吗?皇军的大洋刀,快着呢,砍掉头,都不沾血的。”
“啥脱清身?八路抗鬼子,还不为咱老百姓?都怕死,都得死。”
张二愣冷不及地插一句,他人年轻,血热。
张二楞是张老六的独生子,更是老夫妻俩的命根子。
“小乖乖,恁咋迷呢?”
徐振山一下子急了,转过身子,对着张二愣说教,“你知道不?日本人是咱的一个唐朝大和尚,带五百童女伍百童男,从蓬莱山,下东洋得来的,这是他们来认姥娘门的,老六,俗话说,外甥是老娘家的狗,打不走,咬一口,让他们撒撒娇,走就是了,都怨八路,硬要扛日,哪有当舅爷的样?”
徐振山脸虽对着张二愣,但话是说给张老六听的,“楞子他娘,您说,是这个理不?”
二愣子的娘,仍旧低着头,没言语。
场子就有点冷。
张老六怕得罪徐振山,只得接上话茬,“认亲不认亲的,哪是咱们管着的?您说是不?咱满头高粱花子的,谁都惹不起,保长兄弟放心,俺爷俩,明一早就下地,去躲清身。”
徐振山高兴了,“哎,老六就是个明白人,这就对啦。”
徐振山说着话,移下炕,在地上,站起身子,拍拍屁股,要走时候,再看一眼张二愣,“小子,别犯二愣子事,逮着八路,皇军可有赏,白花花的大洋,可能娶着俊媳妇哩,记着啦?”
说完,徐振山摆摆手,躬着腰身,转身走了。牐
逃难,就象瘟疫一样,有传染性,有这么一两家一带头,别的人就怕了,也就不敢再待家里去,虽然内心里向着八路,可这兵荒马乱的,惹了谁,都是杀头的罪。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不会考虑太多的主义之类的事的,只要地还在,以后不管谁坐江山,总得需要种地的,只要躲开这一段风头就行了。
于是,能走的,都走光了,集市自然也停了,路上拉货的马车也没了,有空旷的土地上,虽还有几个稀落的身影,那是几户家里确实穷,又没亲友可靠的,横下一条心留下来,无奈何地,打整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地。
天刚擦亮,张二楞就扛着锄头出村了。
张老六怕他愣愣唧唧惹出事,天不亮,就喊他起来,到野外去锄地。
冬天的田野,本来的就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一片枯黄,一派寂寥,除了麦苗,就是老北风的呼啸。
张二楞知道,这是爹怕他惹事,打发他外出躲灾难的,张二楞虽然楞,但懂事儿,也就顺从着来到了野地里。
到了田地里,张二愣子,呼吸了几口早上的空气,爽一爽精神。
这几天的,空气里,都有一股硫磺味,自然是从湖边上飘过来的,只是今天,这股味道稀多了,还是甜腥腥的味儿,好闻呀。
在这里锄地,比在家里憋闷强。
张二愣子瞎想了一会儿,收收神儿,认了地垄,锄开了地。
麦地,虽然冻着,但是,锄头一下,满是的松软,跟着的,是杂草的根儿,泛着白,迎着绿,翻出了地面上。
张二楞越干越喜欢,锄出来的田地,越来越长。
渐渐地,张二楞闻到了一股另外的味道,先是没在意,后来,越闻越清晰,是人的血腥味儿。
就有些奇怪,于是,顺着这股味道,沓下身子走着闻。
终于,借着初升的光线,隐约看到了一片殷红的血迹,当然,他立即清楚了,这意味着什么。
年轻人,一种天生的好奇和大胆,驱使着他继续往前走。
就这样,张二楞,顺着血印,走到了一个秫秸堆前。
那是自家秋季的高粱杆,猛然间,呆住了,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凝固起来。
张二愣看到了一支黑洞洞的枪口。
一只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地对着自己。
第七节、落难的张蕴涵遇上了张二楞()
第七节、落难的张蕴涵遇上了张二楞
面对着枪口,张二楞再没了村头打架的楞劲,只是死死地盯住枪口,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感到口干舌燥,喉咙里向被塞了什么喘不过来气。
一句低沉的声音,“蹲下!”
张二愣呆呆地蹲下来,足足怔了有一分钟,才看清,拿枪的人,是一个女的,鹅蛋脸,大眼睛,乌黑的头发,长得俊美,只是脸上烟迹浓重,灰布八路军装上,被挂破了好几道。
她,斜卧在秫秸堆边上,身上并没有受伤的迹象。
在她身边,还躺着另一个人,一样的八路军装,混身的血迹,脸色蜡黄,艰难地喘气。
于是明白了,她在照顾一个重伤员。
女八路盯着他,两人对视着,都没有说话。
这样,过一会儿,女八路开了口,“你是这个村的?”
“俺住这村里。”
张二愣费力地咽口唾沫,结结巴巴地答。
“大早上,出来干嘛的?”
“种……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