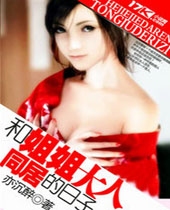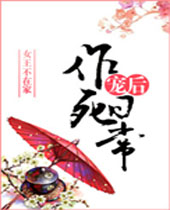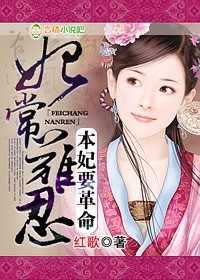刘备的日常-第6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幽州牧王允,冀州牧桓典,一并入朝为九卿。九卿乃中二千石官,自也是荣升。
二人奉诏回京,蓟王亲为饯行。又命水军楼船护送,再赠九坂悬楼,令其栖身。自二人到任,安土息民,吏治清明。萧规曹随,与蓟国相向而行。幽冀二州,吃穿用度,衣食住行,皆已趋同。律法规章,亦比照《蓟法》。赀库更是遍地开花。打击豪强,肃清宗贼,不遗余力。王允、桓典,皆是强项令。无私铁面,不徇私情。上行而下效,河北大地,毒瘤顽疾,被二人并蓟王,联手肃清。
蓟国“圩田制”,正全面推行。
送别二人,勃海王相徐,又行将到任。勃海国与蓟国毗邻。国相徐,入乡随俗,亲赴临乡,觐见蓟王。
徐,字孟玉。广陵海西人。前度辽将军,徐淑之子。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有其掌勃海诸事,刘备自可安心。蓟王今为托孤重臣,权倾朝野。官吏前来拜谒,看上去乃例行公事。实则不然。
皆是假拜谒为名,行认主大礼。
天线有识之士,人尽皆知:今汉气数已尽。忠于汉室的志士忠臣,转投蓟王门下,欲匡扶明主,三兴汉室。一言蔽之,人心向背。
徐自不例外。待皇甫嵩、朱到任,亦如此这般。蓟王刘备,又焉能无觉。
更何况,凡遇河北之事。少帝必遣黄门令,车驾二崤城,询问蓟王之意。由此可知,洛阳朝堂,对蓟王是何等敬畏。事已至此,多说无益。矗立观天阁上,蓟王忽生一丝寒意。
从此往后,有进无退。
1。124 事与愿违()
永乐宫。
董太皇三卿,与骠骑将军董重,悉数到场。
帘后太皇董太后,面沉似水。帘外众人,如坐针毡。
只因不知何人,书朱雀阙。言:“民不聊生,长乐、永乐卖官贩爵,鸡化,乃妇人干政,所致也。”
兹事体大。值班中黄门,急忙入宫通禀。三宫本欲息事宁人,奈何“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出半日,洛阳城已人尽皆知。
遥想先帝年间。亦有人书朱雀阙。引宦官大肆海捕,牵连者数以千计。
旧事记忆犹新,今朝又出此事。鞠城兵乱,惨痛未消。洛阳民众,焉能无惧。
阙书,矛头直指,太皇董太后及何太后。三宫鼎立,共辅少帝。平衡朝野,势均力敌。本是治国良策,续命良药。岂料将将开年,便有人迫不及待。朝政日非,国祚不继。汉庭沦落至此,虽是天灾,更是**。
朱雀门,为北宫之南门。门侧高楼,称朱雀阙。因历代帝王出入,多经朱雀门,故此门最为尊贵。建造亦格外巍峨壮观。“偃师去宫三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朴与天连。”
书于此阙。除去醒目,亦想令少帝出入时可见。
“奸佞之辈,何其多也。”董太皇切齿生恨。
“太皇息怒。”董重劝道:“若有损圣体,徒令小人得意。”
“骠骑将军,所言极是。”永乐少府曹嵩亦劝:“太皇且息雷霆之怒。”
“为今之计,该当如何。”深吸一口气,强压心头之恨,董太皇问道。
“三宫鼎立,不可示弱。亦不可,持强凌弱。公事公办。当交有司,彻查背后主谋。”曹嵩答曰。
“少府,所言极是。”董重亦道:“何太后,亦牵连其中。且看西宫(长乐宫)如何应对。”
“卑不谋尊,疏不间亲。”董太后,恨意难平:“先时阙上所书王甫、曹节,一介家奴耳。如今竟胆大包天,以下犯上。直书二宫帝后。诸君以为,背后主谋,是何人也。”
“这……”董重欲言又止。其中深意,今时今日之董骠骑,又岂能不知。
“卑不谋尊”,便是后世所谓“对等原则”。如此说来,先前书朱雀阙者,必是宦官或朝臣。今日书朱雀阙者,多半是汉室宗亲。三宫鼎立,二宫并书阙上,唯长信宫,独善其身。董太皇言下之意,殿内众人又如何能不,心知肚明。
曹嵩答曰:“太皇,切莫起疑。此事颇多蹊跷。老臣窃以为,若真乃长信宫所为,岂非太过明显。”
“朕,亦如此想。”董太后心领神会,这便悄然收拢怒气。
“二桃杀三士。”永乐卫尉董承,忽言道。
“此话怎讲。”董重忙问。
“三宫鼎立,人尽皆知。贼人却只书太皇与何太后,唯窦太皇未曾提及。臣窃以为,此乃贼人有意为之。”董承言道:“我等,万勿中计。”
“然,亦不可不察。”董太皇这便下诏:“命司隶校尉袁绍逐捕。十日,不,五日一会。”
“喏。”
长乐宫,长秋殿。
气氛同样肃杀。
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长乐少府袁逢、长乐卫尉蹇硕、长乐太仆郭胜,悉数在列。
“何人所为。”帘内何太后,低声相问。颇多心平气顺。
大将军何进,起身言道:“无胆鼠辈耳,太后实无须在意。”
“此事已满城风雨。然,朕深居简出,卖官干政,从何说起。”被奸人污蔑,何太后竟不动气。果然今非昔比。
长乐少府袁逢,起身进言:“太后所言极是。老臣窃以为,贼人之所以牵连附会,正是其阴谋之所出。”
“愿闻其详。”何太后问道。
“老臣以为,贼人将太后及董太皇,并书阙上,却独遗漏窦太皇。乃有意为之。无非是无中生有,挑三宫争斗,坐收其利。”
“贼人何所求。”何太后又问。
“恕老臣,不得而知。”袁逢答曰。
何太后,又看何进:“大将军知否。”
“臣,倒有所得。”大将军何进遂将临行前,长史许攸之言,娓娓道来:“所谓‘卑不谋尊’。宫中家奴,焉敢大逆罔上,诬陷其主。臣窃以为,此书,必出汉室宗亲之手。”
何太后轻轻颔首:“继续说来。”
轻咳一声,何进再接再厉:“汉室宗亲,所怀不满,皆在书中:‘卖官贩爵’、‘妇人干政’。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暗藏私心。乃因‘卖官贩爵’、‘妇人干政’所得之利,未能分润宗室罢了。”
“哦?”此乃何太后,未曾料到。
“黄巾乱后,群盗蜂起。万民饥流,道路断绝。洛阳贵胄,食俸大减。唯举债度日。传闻,先帝暗授巨资与金市子钱家。贳贷宗亲贵胄,得海量子钱。重利盘剥,乃至无法偿还。不得已,唯将食邑,质与子钱家。奈何,金市子钱家眼高于顶。只贳封君县主。诸多乡亭小侯,皆未能如愿。故奋笔书于阙上,以泄心中不满。”
略作思量,何太后欣然点头:“府中何人进言。”
大将军不敢隐瞒:“乃我长史,南阳许攸。”
“可是同乡。”何太后又问。
“正是臣之乡党。”何进对曰。
“此人当可重用。”何太后言道:“待大将军方便,引来与朕一观。”
“喏。”大将军这便领命。
“若如大将军所言,此事当如何转圜。”
见太后看来,少府袁逢,再起奏道:“若真乃宗室不满。只需善待,便可消除。”
何太后又看何苗:“骠骑将军,以为如何?”
“臣……”何苗欲言又止。
“但说无妨。”何太后言道。
“所谓‘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臣,窃以为。金市子钱家,之所以不愿贳贷小侯,乃因无利可图也。天下小侯,何其多也。食邑散落大河上下,广布南北东西。需海量人手代为打理,故无从收拾获利。”偷看何太后表情,何苗咬牙道:“太后若救天下小侯,需广费钱财。若一二载,便也罢了。然若遥遥无期,太后纵有万贯赀财,又如何能够。”
何太后欣然一笑:“大将军以为如何。”
来时,何进便已有定计:“始与朝政,使先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论‘卖官贩爵’,永乐董太皇,尤胜先帝。传闻,近日又假勃海王年幼,无法就国,已暗将勃海七城,质与子钱家。为期十载,得琉璃宝钞十亿。料想,此事宗室亦有所闻,故才奋笔书于阙上。”
“勃海王,生于光和四年。十年之后,亦不过十五少年。神鬼不知,得钱十亿。永乐董太皇,好算计。”何太后一声冷笑。
1。125 息事宁人()
书朱雀阙之谋,之所以令张让、赵忠,事与愿违。原因有二。
“卑不谋尊”的政治对等原则是其一。“敢逆汉室者,必出汉亲”。于是自然而然,将目标人群,圈定为洛阳贵胄,汉室宗亲。
“列候次减”的利益分配模式乃其二。“天家吃肉,我喝汤”。“吃肉喝汤”,便指自上而下,分封制的利益分配。
然,先帝母子,却赢者通吃。卖官鬻爵也就罢了,还趁人之危,暗放子钱。将宗室贵胄,一二百年积攒的家底,吃干抹净,不留一个铜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逼不得已,唯将食邑质押子钱家,苟且续命。奈何子钱家,挑肥拣瘦。只贳封君县主,乡亭小侯一概不取。三宫少帝,不闻不问。任我等自生自灭。
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于是乎,便有了“书朱雀阙”之事。
道理都通。乃至何太后,深信不疑。且又误以为,先帝《子钱集簿》,今握于太皇董太后之手。又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若要息事宁人,平宗室众怒。唯太皇董太后出手,命金市子钱家贳贷小侯,自当迎刃而解。
长乐太仆郭胜,进言道:“先帝《子钱集簿》,究竟握于谁手,此事尚无定论。且,是否有《子钱集簿》,亦未可知。若董太皇咬死不认,又当如何?”
何太后冷声道:“母子卖官贩爵,敛财无数。惹天怒人怨,先帝崩于困龙台,犹不悔改。今洛阳宗室亦怒而发声,窦氏如何还能稳坐高位。”
车骑将军何苗,急忙起身进言:“如太后所言。若令洛阳宗亲,‘骨肉离心,人有畔(叛)志’,社稷危矣。”
“事关宗室存续,社稷存亡。不可不察。”长乐少府袁逢,亦起身言道:“料想,只需好言相劝,董太皇必当领会。密令洛阳子钱家,善待宗室诸侯。”
“此事,宜当谨慎。”长乐太仆郭胜劝道:“老奴窃以为,太后切莫当面提及《子钱集簿》之事。”
“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太后冷笑:“母子既然做得,又如何不能说得。”
“当真说不得。”何苗亦苦劝:“料想,太后便是提及,董太皇亦百般抵赖,断不会认。只因,如若认了,便坐实朱雀阙书上‘卖官贩爵’、‘妇人干政’之言。乃至德行有污,颜面无存。若引百官劾奏,宗室群起而攻。董氏如何还能窃居太皇大位。”
何进亦随之进言:“车骑将军所言极是。太后万勿逼迫太紧。反令董氏一门恼羞成怒。”
“国祚至此,夫复何言!”何太后一声悲叹。
见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齐齐来看。
长乐少府袁逢,遂起身进谏:“太后息怒。今少帝继位,窦太皇垂帘。必不会重蹈,先帝覆辙。只需忍耐数年,则万事无忧矣。”言下之意,道路曲折,然前途光明。
可谓一语中的。何太后言道:“既如此,诸君以为,该当如何。”
长乐少府袁逢,计上心来:“何不请窦太皇出面,趁三月上巳节时,三宫与少帝,泛舟濯龙园。席间,太后见机行事。料想,董太皇必欣然悔悟。”
“少府乃老成谋国之言。”何进大喜。
“臣,附议。”何苗亦无话可说。
“如此,朕便依计行事。”何太后轻轻颔首。
“太后明见。”众人下拜。
数日后。北宫,永巷,黄门署。
张让、赵忠,相约密会。
“如何?”赵忠忙问。
“事与愿违。”张让摇头叹气:“三宫皆无动静,亦无风传。唯董太皇诏命司隶校尉袁绍逐捕,五日一会。”
“怎会如此?”赵忠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实不知也。”张让苦笑:“天亡你我,非人力可为。”
二人枯坐,相对无言。
“先前,家中来人,言颍川旧宅尚在。”不知过了多久,张让忽言道:“不如上书乞骸骨,就此归乡,或可得善终。”
赵忠惨笑一声:“你我刀锯余人,树敌无数。天下恨不能食肉寝皮。若离深宫,不出洛阳八关,必满门惨死,如何善终。”
“唉,事已至此,又当如何。”张让唏嘘。
“若不想隐姓埋名,举家避居深山,世代与野兽为伍。唯有放手一搏,有进无退。”赵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