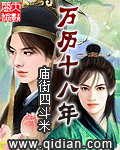崇祯八年-第10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盐商们对大老爷们自是不缺年节之礼,并且礼物很厚重。比如名家书画,前朝古董之类的贵重物品,金银相对给的少。
但是给书办司吏们的则是结结实实的真金白银。但凡是遇上胥吏们家中有婚丧嫁娶,生日寿辰的大事,盐商们都是出手大方,并且定要当着来宾面前大声唱出礼单,好让主人家觉得倍有面子,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同时盐商们还会拿出钱财资助家境贫寒的读书人,用烧冷灶的方式来帮助对方,以期将来被资助者飞黄腾达时,自家人能跟着沾光。这种事情在江南一带很常见,也的确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
至于有些举子喜欢打着旗号邀名,举办各种诗会文会所需的费用,也是盐商们出资赞助。
这些举措加在一起就产生了很好的效应,在江南一带,盐商在官府士林中的名声非常好,双方各取所需,渐渐的紧密相连在一起。
崇祯之所以想慢慢挤压这个团体的利益,而不是明目张胆的派人抄家灭族,是不想激起大的民愤,引发江南局势的不稳,从而导致朝廷赋税漕运受到严重破坏。
江南要是再乱了,就算能调兵镇压,但也会使本就严重依赖南方输血的朝廷陷入瘫痪状态,也让缺粮的北方彻底糜烂。
拿下淮安盐提举司后,这个团体自会嗅到危险的味道,这让一贯轻视并喜欢要挟朝廷的他们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民变就是他们最喜欢的手段,也是对付朝廷最有效的方法。他们知道朝廷最怕江南动乱,如果不是崇祯穿越而来,这种行为的确是捏住了朝廷的命门。
崇祯就是想逼着他们发起民变。
淮安府紧邻盐商聚集的扬州府,陈奇瑜坐镇淮安,手握重兵,只要情报掌握准确迅速,民变发起之时便是参与者覆灭之日。
按照以往的惯例,盐商团体绝不会想到朝廷会派兵弹压。
从来都是民变一起,江南士林对朝廷一片讨伐之声,利益相关的地方官纷纷上本,要求严惩北盐南运的幕后主使,还大明一个风清气朗的如画江南。
之后皇帝和重臣们在慌乱之际,会用妥协来回应此次事件,然后民变迅速消弭,大家酒照喝舞照跳,只是北盐会彻底消失,一切恢复到原点。
现在崇祯已经知道对方的底牌,需要做的无非是掌握出牌的时间和主使者而已。
盐商们目标太明显,只需要让锦衣卫盯住近期活动频繁的有关人员便可。现在就要跟跟陈奇瑜打好招呼,让其早做准备,只要有了锦衣卫的情报,不必调集太多官军,擒贼擒王就可迅速平息这场祸端。
之后就是秋后算账了。
锦衣卫出场,将涉案官员商人逮获便可,这些人毫无抵抗力,也不敢公然对抗朝廷。
罪名就是煽动民变对抗朝廷,图谋不轨。或许锦衣卫会从某些人家中查获与流贼暗中来往的证据。
只要按上通贼的罪名,谁敢出面为其说话讲清这,统统以同党论处。
嗯,就是这么办。
只要两淮盐使司上下都拿下了,两淮盐场就可以全部拿过来,灶户将成为历史。留下一部分人晒盐,其余的或是分派查没的田地,或是新垦荒地,或是去工坊劳作,从灶户转化成农户就成。
当然了,安家银还是发的。拿到银子,民间的怨言就会减少,等过几年他们适应了新的身份,以前的不满早就烟消云散了。
这回抄家又是一场大丰收,两淮盐使司衙门里上下都不能放过。
那些中下层官吏,家产未必少于主官,日常他们上下其手,把该属于朝廷的钱财落入自家囊中,这回该还回来了。
盐商要分别对待,不能株连,主使者也就几个,其他的都是胁从。
把为首几个办了就行。
生员中要是有人跳出来,那就革除功名好了,就当是给东林党敲敲警钟。
别以为江南就是你们的,这大明还是朱家的,还是朝廷说了算。
第140章 宋应星()
江西分宜是个风景如画的小县,人口不足三万,山多地少,是一个典型的下县。
由于地处山区,想要大力发展农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文官集团又向来轻商,所以分宜多少年来经济相当落后。知县也基本是会试榜尾,在朝堂上没有关系的同进士担任,来此意味着仕途前景十分的暗淡。
分宜在嘉靖朝时出过一个至今本地人都引以为荣的名人严嵩严惟中。这位在嘉靖朝担任首辅长达二十几年的大人物,结局却是相当悲惨。被次辅徐阶打到后流原籍监视居住,后在某些人的刻意嘱咐下,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生生冻饿而死。
最讽刺的是,在众人口中的堂堂奸相,最后抄家仅得银三万余两,而以清廉著称的徐阶,仅在老家松江府就有几十万亩的良田。按当时市价四两银子一亩计算的话,徐矮子也已经是等于几十个严惟中了。
也是受到严嵩的拖累,自打他被定性为奸臣之后,分宜便一直不受朝臣的待见,在严嵩执政时还算不错的分宜逐渐衰败下来,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在城中心县衙东北角的一个院落里,任职分宜县教谕已近三年的宋应星,正在屋内的一张破旧的书桌上奋笔疾书。
年已五旬的宋应星两鬓已现斑白之色,黧黑的脸色配上平淡无奇的无关,使他看起来不像一名文人,倒是更像一名老农。
自从万历四十三年以江西第三的名次高中举人后,他和兄长宋应升先后五次赴京咱家会试,但两人最终都是名落孙山,从此两人遂绝了科举之念,改为一人出仕为官,一人回家服侍年已七旬的老母。
崇祯七年宋应星老母生病,家境窘迫的宋应星,才在离家乡不远的分宜寻到这么个不入流的职官位子,好歹能有份微薄的俸禄养家。
时已近午,已经动笔两个时辰的宋应星才停下写作。将毛笔搁在笔架上后,用手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心中感叹:不服老不行,毕竟是五旬的老人了,写文章时间一久,眼前的文字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他拿起刚刚书写的一篇文章,从头到尾检视一遍,以防有错漏之处。
片刻之后验看完毕,宋应星满意的点点头,轻轻的呵气将墨迹吹干,然后将这篇新作归拢到厚厚的一摞文稿中。
终于写完了。
耗时两年,费尽自己无数心力的书稿今天正式完结,自己总算是完成了圣人所言的三不朽中的一件………立言,也算是没有白读这么多年的圣贤书了。
回想两年来写书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宋应星暗自叹了口气。
因为手中并无多余的银钱,除了购买必要的文房四宝以外,书中许多物品的制作过程无法加以验证。虽然流程看似顺畅,但结果却无从得知。
例如文稿中有一篇名为甘嗜的短文,记录的是如何种植甘蔗,收获后如何制成蔗糖的方法。
这是他与在肇庆府恩平县担任知县的兄长应升书信往来中听到的,可具体如何操作才能制出蔗糖,只有亲自实践过方才得知结果。
至于他想与有相同爱好的友人辩论书中所记的真伪,可是却没有类似的场馆实物来实施。
要是如扬州盐商那般豪富该多好啊,手中就可以有大量的银钱供自己支配。到时寻一处地方,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场院,把书中所记各种事物全部验证一番,以便使得后人少走许多弯路,让农家学成一项小技便足以养家,全天下将会有多少贫苦人家从中受益,那该是多么好的一种景象。
不管怎样,自己都要将此书刊印天下,让更多有志于此的人士利用手中资源去实践、去改正、去创新。
这才是立言的本质,而不只是为了扬名方才立言。
他从心里鄙弃那些只知其味而不知其源的纨绔子弟,以及那些终日埋首经中的酸腐文士。
难道这些人不知道其日常所用,均是通过农人匠户的各种劳作而产生出来的吗?
其所食所穿所用,哪一件是看书后凭空出来的?不都是被他们视若粪土的贱民用血汗制造而成吗?
那些内阁重臣、府县主官口口声声悯农惜农,可有哪一个是真正把农户放在心中的?
除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官府税赋,就是底层胥吏的盘剥勒索,个个如同敲骨吸髓的恶鬼一般。其种种所为,哪一点像是爱民如子的样子?难道圣贤们在书中就是如此教导他们的?这么多年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忽然一阵雷鸣声从腹中传出,打断了宋应星思考。
县衙有供应简单的饭食,虽然难得见到荤腥,但米饭倒是可以管饱。
妻子留在家中照顾老母,宋应星是孤身一人来到分宜。
因为并无多余的银钱雇请仆从婢女,这两年宋应星都是一个人熬过来的。
这些对于习惯了清贫的他来讲,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他现在考虑的是去哪里寻求银钱,把他的文稿刊印出来。
兄长应升的薪资大部分也要寄回家中,以供养老母和几个在家务农的兄弟。
家中兄弟四人,除了他和大哥应升在外为官,二哥和四弟都在奉新老家操持田地,两人家中也是人口众多,侄子侄女加起来足有十余口,指望田地那点产出仅仅裹腹而已,日常其他花用只能靠他和兄长的月俸度日。
油盐酱醋、人情往来、修房盖屋,婚丧嫁娶,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开支,也是必不可少的。
向来清廉端肃的宋应升不会有太多的额外收入,在外为官几年,身边也只有一名老仆跟随服侍,家中大嫂侄儿一直待在老家。
县教谕属于没有品级的职官,每月只有一两七钱的月俸。偶有家境宽裕的生员送一点年节之礼,无非是腊肉点心之类的,从无有人送过银钱与他。
即便这点微薄的收入,宋应星每月也要攒下一两,攒够五两银子,便托人捎寄回家,好让家中宽裕一分,可以让老母能吃点好的。
对了,该给这份书稿起个什么名字呢?
宋应星忘了腹中饥饿,皱眉苦思起来。
既然是格物之书,那就不能用什么集什么录之类的名称。
到底用何名称为好呢?
易经系辞有云:天工人其代之,则必与天无二;格物需开物,方能成务也。
有了!就是它!
世间万物自有规律,格物方能致知,而致知便能进一步提高自身学识,然后再用实践将其实现,所思之物便会制造完成,并且其精巧更胜天然!
天工开物!
对!就是天工开物!
此刻的宋应星手舞足蹈,开心的像个孩童,要不是脸上的皱纹如同深沟一样的话。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像是有人小跑着进了院子。
宋应星停下动作,心里略感奇怪。
平时很少有人来到这里找他,县里的公事与他无关,他也不喜与生员外的人交往。
“宋教谕!知县大老爷有请!”
一个差役气喘吁吁的站在门口喊道。
宋应星整了整衣冠,沉声道:“你可知知县大人何事找我?”
“京城来人了!说是奉命前来接宋教谕前往京师!宋教谕,您老要发达了!”
差役满脸喜气的开口道。
宋应星一愣,京城来人?怎生回事?我在京城并无亲友,也无同科同年,谁找我呢?
当宋应星来到衙门二堂时,分宜知县赵逢春满脸堆笑着起身相应,口中道:“长庚兄,快快请坐!京师两位上差前来寻你,言说乃圣上所遣,请你到京师有重用!恭喜恭喜!”
宋应星目光看去,两名身穿蓝色罩甲的年轻人端坐在椅子上,正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
见宋应星用莫名的眼神看来,两名年轻人同时起身拱手行礼,然后其中一人开口道:“可是宋先生当面?某二人乃锦衣卫北镇抚司缇骑,某乃校尉李成,彼乃校尉徐松。某二人奉上命前来接宋先生至京师一行!”
宋应星闻言不由更加惊诧。
锦衣卫不是已经式微了吗?怎地突然出现在偏僻小县,且还是专程前来寻我?我不过是一不入流的杂官,日常也未犯何忌讳呀?
李成见其神色,自是明白其心中所想。于是笑道:“宋先生切勿多虑,实不相瞒,某二人乃是奉圣喻前来。圣上闻听先生大才,欲召先生前往京师另有重用,先生要是无他事,还是收拾一下,咱们尽快赶往京师为好!”
旁边的知县赵逢春用羡慕的眼光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个宋应星性格古怪,平素很少与人交往。就算在一个衙门中,他和宋应星也只见过寥寥数次,那几次也都是在县试时的公众场合,两人私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