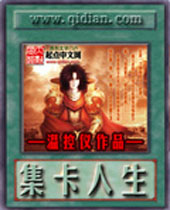余杰杂文集-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你没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是听得的?”
对:“也有翻看书籍、地图查考得的,也有问得的。”
问:“香港安船不安船?”
对:“臣赁法国公司轮船,轮船总有载货卸货、载人下人等事,一路口岸必有耽搁,但皆由该船作主。”
由此可知,慈禧不仅对曾氏的出使路线饶有兴趣,且关心曾氏的知识来源。显然,慈禧本人也在主动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以便在决策时能胸有成竹。
慈禧还询问了曾纪泽在外国如何递国书,以及外国从事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的情况:
问:“递国书的日子,系由你定?系由他们外国人定?”
对:“须到彼国之后,彼此商量办理。”
问:“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对:“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也不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
此时,慈禧掌握国家权柄虽已十多年,但她并不清楚朝廷体制中“总理衙门”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更不用说洞悉西方诸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架构了。最高决策者基本知识的欠缺,不是个人问题,对朝廷可能带来致命结果。但慈禧的这一欠缺也有可以理解之处:当年朝廷商定设立总理衙门时,慈禧还是一名把主要精力用于抚育幼小皇子的贵妃。所以,在以上的对话中,才出现“外国也有总理衙门”这个显得颇为可笑的问题——总理衙门乃是清廷在西方压力之下被迫成立的,其仿效西方国家外交部的体制,只不过用了更为中国化的名称而已。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等人联名向咸丰帝呈奏《统筹洋务全局斟拟章程六条》一折,请求“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天后该主张在热河王大臣会议上通过。1861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直至1901年外务部成立),它对外交及其他洋务活动无不包揽。总理衙门成立之后,清朝的内政大权由军机处掌握,涉外事务则归总理衙门,故被称为“洋务内阁”,但军机处仍参与重大的外交决策。(参阅于建胜、刘春蕊《落日的挽歌——十九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89—91页。)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标志性事件。唐德刚指出,中国在秦以前存在着发达的外交体制和外交思想,但“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的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这也是蒙古黄种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51—52页。)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只有“内交”而没有“外交”的时代——“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就是没有‘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同前,第52—53页)这样一种延续两千年的政治传统,在十九世纪中叶遭到惊涛骇浪的冲击——不用说刚刚秉持国政的慈禧太后,即便是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转世,也未必能迅速理解并熟悉一整套仿佛从天而降的“洋务”。对于慈禧惊人的“无知”,后人不必用过于苛刻的眼光来批评之。她身处历史之中,而且已经在主动地作出某些调适了——最高层在知识和观念上的调适,往往又比一般人更为困难。(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此困难:二十多年之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企图在觐见的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与日本的国书、定制世界地图等细小的事件上体现“外交新政”,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观念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但即便是在这些细小问题上,他也走得太快,与总理衙门、军机处产生不小的矛盾。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传统深重的国度在向近代转型时的艰难与无奈。参阅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而对曾纪泽来说,与这样一位极为精明又匮乏基本“常识”的太后对话,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既要照顾太后的权威和自尊心,又要尽可能多的向她传达新知识、新观念。每句回答都要做到含义尽量丰富,却有点到为止。
(二)士大夫参与外交事务所面临的道德压力
在慈禧与曾纪泽的对话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士大夫参与外交事务所面临的道德压力。曾纪泽以“拚却名声,顾全大局”八个字来概括从父辈曾国藩、郭嵩焘到自己这代士大夫介入洋务的心路历程。以下这段话可以说字字皆血泪也:
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名声,以顾大局。七十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免冠碰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拚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拚了名声,也还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首先,曾纪泽指出办洋务难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这两个方面,他尤其强调后者,力陈偏执的仇外、排外主义对国家有大害而无裨益。慈禧本人没有受过多少孔孟之道的熏陶,她从女性的直觉出发亦认识到“办洋务不易”。当然,慈禧自身的经历使之与洋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愤而表示“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却”——她的丈夫咸丰帝就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都城、被迫逃到热河之后而悲愤而死,她本人则熬过了一段“孤儿寡母”的惊惶岁月,方夺取权柄。但是,慈禧也认识到,对付洋人“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因此她积极支持自强运动——除了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个短暂的时期内陷入某种歇斯底里的情绪之外,在君临天下的近半个世纪里,她对西方的政治、文化还是持较为开明的姿态。
慈禧个人的开明并不能改变道德主义对洋务强大的压力,道德因素始终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力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在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皇帝之间不仅是权力同盟,更是“道德同盟”——他们共同营建出一套庞大的道德伦理体系,并以之作为治国的标榜:“皇帝高唱继承圣王的论调、标榜德治主义以求得王朝的安宁保障;知识分子通过经典的学习、古圣王事迹的讲述不断向皇帝灌输德治观念以期杜绝皇帝的专横。在这里,学问连权力、权力通学问现象已表露无遗。所以,学问并不仅仅是表现权力,其本身就是权力自身。作为权力的学问,是对毫无知识的人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31页。)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和信仰为精神依托,故只能深陷于权力的泥沼中,心甘情愿地成为皇权价值——即日本学者三石善吉所说的“皇帝主义原则”——的阐释者和捍卫者,“知识分子主要地来自于农民阶级,但他们虽也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观念,却更多地重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德治主义是一个以道德为轴心的金字塔作为前提的思想体系。”(同前,第131页)
于是,“忠君爱国”成为士大夫的最高人生价值,它被赋予了高昂的道德激情。以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为例,尽管他是中国士大夫中少有的实现了“立功、立言、立德”的“一代完人”——他是再造皇朝的首要功臣,在儒学上的建树足以同历代大师媲美,个人品格也几乎无可指责,但以此丰厚无比的资源,依然不敢在洋务上往前走一步,晚年甚至因为处理天津教案向洋人让步,使名声受到巨大损害。以曾国藩这样一个自始至终坚持“中国中心主义”的名臣,尚且在道德舆论的压力下说出“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八个字来,可见洋务之难难于上青天。大部分中国官僚和士大夫,他们的开明有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必须承认和捍卫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先进性”。敢于跨越此一底线的士大夫可谓寥若晨星。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分析曾国藩的变革思想时指出:“尽管他始终具有中国人的自信心,但曾国藩对作为对手的西方还是很了解的。这个对手是如此令人可怕,以至于使曾国藩感到有必要大力倡导将西方的物质文明纳入中国文明。这一倡导虽然意味着将西方作为一个价值中兴来看待,但它仍然保留了中国最基本的优越地位。这样,在这种广泛的折衷主义中,我们发现简单地接受在理性上具有说服力的西方价值,他关心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要求,而是如何使它表面上合法化,以便被中国人所接受。”(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46页。)即便是这种“折衷主义”的、富于策略性的学习西方,也得付出失去道德制高点的沉重代价。因此,大部分官僚与士大夫,在意识到近代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依然不放弃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捍卫。按照日本学者三石善吉的说法,这种维持道德优越感的近代化是一种“内发性发展”,即“在力图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地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文版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这种“文化基础”,一言以蔽之,乃是“文的传统”。于是,中国的近代化无论怎么努力也只能达到“下半身”的近代化,一有风吹草动,其成果则迅速化为乌有。
曾纪泽列举了两个人物的遭遇来说明办洋务非得有“拚却名声,顾全大局”的思想准备不可,一是其父曾国藩,二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长辈和即将同他交接驻英法公使职位的郭嵩焘。曾国藩和郭嵩焘办洋务遭诋毁的遭际,均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涉足洋务需要莫大的勇气——比牺牲性命更大的勇气,即牺牲士大夫最珍惜的“名声”的勇气、甚至被冠以“卖国贼”之名亦不退缩的勇气。虽然当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尚未形成,但古已有之的帝国的文化傲慢及道德优越感仍然难以撼动,它们成为士大夫心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替国家办事,如果要办到被骂作“卖国贼”的地步,这将让所有士大夫都会为之犹豫、为之踌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