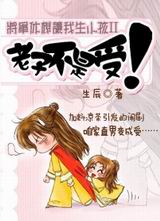我生命的两极-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地人把这一类面具称作“脸子”或“脸壳”、把雕脸子的汉子称为“雕匠”。随着出访法国和欧洲,傩戏大盛,一时间,雕匠顿时也跟着声名远扬,大受欢迎,被四乡八寨的老百姓请了去,酒肉款待是不消说的。他们也便纷纷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创造着新的品种和样式。于是乎,用白杨木、丁香木雕刻而成的丑鬼、道人、女将、小军、忠臣良将等等千奇百怪的脸子就在方圆数百里内的村村寨寨传了开去。
有了脸子,讲究的地戏班子,喜欢攀比竞争,遂而就逐渐配齐了包头的黑布或是黑纱,黄花背旗野鸡翎,大红绣花的背板和水红上衣,浅绿的战裙,黑底绣花腰带,甚而至于扇袋、香包、银铃铛、竹骨扇,一应齐全,披挂整齐。
有了配备齐全的行头和五颜六色的“脸子”,就可以演地戏了。
开演地戏,封箱的“脸壳”在开箱之前,必须得依照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点蜡烛烧香,供滴血雄鸡。进了场,还须“扫开场”,演出之后还得“扫收场”,连带着祭土地,给村寨上的家家户户招财进门,所谓“日落黄金夜落银,牛成对来马成群”。并保佑全屯堡的良民百姓平安富足,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如此重大的场面和活动,岂能不造成声势和影响?只消哪个屯堡的地戏一开锣,四乡八寨都有人赶了去凑热闹,就如同城里人看灯会、庙会、逛小吃街的心情一样。
安顺的地戏如同出土文物一般扬名于世界。在乡间的地戏纷纷扬扬越闹越红火的那几年中,安顺附近的黄果树瀑布、犀牛洞、天星桥和龙宫等等引起世人瞩目的景点,正被有计划地辟为西线风景区,吸引众多省内外、国内外的游览者。先是那些被一股一股西洋风吹得晕晕乎乎的美术界人士对“脸子”发生了兴趣,其中一些颇有见地的美术家们被那些返璞归真的“脸子”所吸引,忽觉得那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嘛!于是乎仿造者有之,受此启发举一反三运用于砂陶、雕塑、绘画创作中有之,很快地携自己的美术新作冲向世界艺坛的也有之。
最大量的,则是在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脸子”在出售。满街比比皆是,四处泛滥。这一现象,究竟是喜是忧,我也说不清了。
屯堡景观
地戏的话题还可以说上几遍,比如说地戏与日本北上川市鬼剑舞的关系,比如说“脸子”上的画法有什么讲究——不过越往下说越说不完,干脆我就打住,让有研究兴趣的人去深挖细探罢。
罕见的屯堡奇观(6)
随着地戏的名声越来越大,去屯堡看地戏的人越来越多,屯堡的景观也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人们对屯堡的历史、对屯堡的文化、对屯堡的生存方式、民俗信仰,都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除了地戏,屯堡还有其他几种民间的艺术样式。前面我提到过的,在白喜场合有人在唱歌,就是一种样式,在当地叫作唱书。传说洪武年间最初在屯堡住下来的“京”族老祖宗们
,看到附近村寨上的少数民族在那里喝酒唱歌、边歌边舞,觉得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相比之下十分枯燥,格外想家。于是就将在家乡学过的说唱词,凭记忆记录下来,边哼边唱,自娱自乐,逐渐地形成了唱本。再根据唱本上的内容,改编成地戏来演。
和唱书形成对照的,就是当地的唱山歌。可以说,一到贵州,最早吸引我的民族风情,就是唱山歌了。贵州的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居住在水边还是山地,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唱山歌的传统。依照他们的说法是,见子打子,见什么就唱什么。唱情歌的时候,更是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本领的时候,随机应变,越是能唱的小伙子和姑娘,越能得到情人的青睐和众人的尊重。
屯堡一带的山歌,具有江南民歌的韵律和色彩,但已经吸收了贵州少数民族山歌的活泼、多变、奔放、自由自在的特点。
这种既有江南风味,又和当地特色融合的文化现象,随处可见。
我第一次深入了解的一个屯堡村寨,叫作“放鸽哨”。乍一走进寨子,看到村边的小桥流水,看到村子中央的池塘,看到房前屋后的竹丛,看到房屋的门洞,还有呈明显江南格调的四合院,里头有朝门、堂屋、厢房。院子里有水井,包括门窗上雕刻的花纹图案,我久久地站在那里,恍然感觉自己走进的是江浙一带的村庄。
直到我在街巷间走久了,看得更细了,我才逐渐发现了这些屯堡中和江南水乡的一些不同之处。比如江南水乡的民居,往往称之粉墙黛瓦,那一片片瓦都是黑颜色的。而在屯堡,虽然也有盖瓦的房子,但大多数房屋,盖的都是页岩石板,大大小小,铺盖得错落有致,远远望去,既是白花花的一片,但又不觉得枯燥,那有弯有斜、有竖有横冰纹般的纹路,映衬在青山绿水之间,别有一番情趣。被不少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典型古城堡的屯堡村寨,既保存着明清两朝的遗风,又融合着西南和江南各自的特色,非常耐看。
至于过大年的时候,家中不许扫地,说是怕把财宝扫走了;五月端午,要吃粽粑,挂菖蒲;生了娃娃,要吃满月酒;等等等等生活细节,则同我们孩提时代经历过的几乎一样。只是讲究的程度不同,江南一带渐渐淡化了的民俗,在屯堡却还完整地保存着。要说差别,最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体现在伙食上,今天的屯堡人,已经和所有的贵州人一样,特别爱吃辣,辣子豆腐、辣子鸡、糟辣椒炒肉片,已是安顺屯堡人的名菜,可以说是无辣不成菜了。
奇特的风情,悠长的历史,古朴的艺术,别致的生存环境,构成了罕见的屯堡景观。这就是我曾经生活了整整21年的那一片乡土,时常在梦境中萦绕不去的山地。把它写下来,也算是我一份心意罢。
(2001年9月)
九寨沟之旅(1)
叶田修完高三的学业,结束了一次又一次考试,我们决定要到九寨沟去。
九寨沟,九寨沟,近些年里,画报、影视、光碟、文字,不知对它的风光有过多少报道了。还有那些已经去过的游客,他们眉飞色舞的渲染,更对这一旅游资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整天迷恋于电脑和影视片的叶田,一听说九寨沟,也欣然答应同往。
于我来说,80年代初期,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一次便不想再失去了。那一回因为从成都去九寨沟,需要两天路程,还得防备泥石流冲毁路基;那一回还因为叶田年幼,家中无人照顾,我得尽初为人父的责任。如今,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叶田已成长为一个大小伙子,而我也已年近五旬,再错过机会,又一个十七八年过去,我就爬不动山了。
那真是山啊,车过都江堰,进入羌族聚居的汶川,成都平原就被逐渐地抛在身后,川西北的山势就逐渐地险峻起来。山野也变得好看起来,变得如文人们喜欢形容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山间公路旁,一条水流湍急、浪跳波笑的江河始终伴着我们。一问,才知这水就是大名鼎鼎的岷江。
但行一声呼,高峡出平湖。
过了茂县,山路弯弯,盘旋而上,翻山越岭爬去的,正是石大关。我想石大关该是“十大关”的谐音罢,车到高处,俯首望去,细细一数,嗬,曲里拐弯的险道,还不止十处。
海拔明显地高上去,不仅人不适,进口的丰田车也像在喘息着爬行。我请郝师傅停车,他挂上最高一挡,车子直驰而去,一直爬到悬崖边的弯道上,才把车子停下。
这是拐上悬崖的高原公路,风似要把人掀翻。我站在路边,放眼望去,不由一阵骇然,陡峭的山崖如同被巨斧劈削一般,直达水波涟漪的一个巨大的海子。稀奇的是,在山脚下还是激流汹涌的岷江,流经海子,却变得温顺、驯服,偃沫息珠,仿佛一下子凝铸于宽大的河谷之中。周围雄峻伟岸的座座大山,一座一座全像被巨斧劈削过一般,挺起玄武岩钢灰色的胸膛,任凭温情脉脉的碧水抚慰着自
己粗蛮的身躯。海子口上,平静的岷江水悠然而至,软如绿缎般平滑地伸展而去。
风吹来,我不由打一个寒噤,回身问郝师傅,这是什么地方?
“叠溪海,”郝师傅说,“1933年,松潘大地震震出来的海子,远近闻名。”
怪不得景观如此奇特。我再细问,郝师傅告诉我,他也讲不分明了。他是在新疆长大的,前些年刚调来西南交大,他说他也没闹明白,松潘离这里还有一百多公里呢,为什么要叫“松潘大地震”?
后边的路侧设置着一些简陋的小摊,小摊上有牛角梳、小藏刀、牦牛尾巴等一些纪念品卖,我走过去,一边询问藏刀价格,一边打听松潘大地震是怎么回事。
几个摊主你一言我一语,将六十六年前的那场浩劫,给我讲清楚了。
叠溪古城,原称蚕陵,公元前就已设县制。震前的古城,坐落于高出江面二百多米的叠溪台地上,城中有繁华街道,茶楼酒肆,有旅社有饭馆,甚至还有驻军一个连和城隍庙。原属茂州(即今茂县)管辖。
1933年8月下旬,一场大地震在瞬间发生,山崩地裂,河谷易容,惊天地动鬼神,叠溪古城顷刻下陷,笔直地跌落下去,城周围二十余羌寨亦全部毁灭。四面的山峰撼动着崩塌滚落,堵塞岷江,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十一个堰塞湖。
遂而一个半月以后,地震形成的海子蓄水日久,又加上岷江源段大雨倾盆,大震之后的余震、小震摇撼江堤,江水骤增,咆哮奔腾,堵江堤坝抵挡不住,倏然崩陷,三海暴溃,洪水激浪排空,倾海涌出,顿时怒涛滚滚,吼声震天,十里百里声可闻。大水所到之处,无论江上索桥、江岸房舍民居,悉数全被吞噬,扫荡殆尽。远在乐山的大佛,拍岸云水也已洗到脚面。
8月、10月两场灾难,死伤共八九千人。
我听得目瞪口呆,风扑上颜面,卷起一阵一阵尘沙。身旁公路上,车前挂着成都—九寨沟的旅游专线大巴、中巴、考斯特,满载着乘客呼啸而过。车上可有人留意这悬崖公路下的海子?车上可有人知道眼前画卷般的风景系大震的遗迹?
我忙叫叶田过来听。这孩子,正捧着大伯伯给他的摄像机拍摄远近的风光。他是在贵州的大山里长大的,从小看惯了各种山的风貌,一般的山势山景,吸引不了他。到了这地方,想必也感觉到这景致有其独到奇特之处。
目斜苍山远,峰峦映湖面。柔波涟漪上,有野鹤拍翅飞过,于水面翻飞点水。清静的溪
流,温顺的海子,雄武壮伟的大山,六十六年的岁月重又使河山显出一派苍翠豪放。
郝师傅在催促上路,我胡乱向争相给我诉说往事“摆古”的男女摊主买了几把小藏刀,匆匆登车赶路。
车拐着弯跃向峰巅,狭窄的路面旁,紧贴着笔陡的悬崖,竖着一块厚实的牌位,上书四个遒劲的大字:神龙牌位。一人高的牌位上披红挂绿,裹着绸巾。几个慓悍的汉子,有的点香,有的作揖,有的虔诚地跪拜在地。他们是在祭奠自己的祖宗,还是在求助神龙莫要发威?
离开嵯峨雄峙、壮美奇崛的叠溪海山水风光,顺岷江峡谷,沿茂松公路,一路前行,直驱九寨沟口。
九寨沟之旅(2)
岷江峡谷,古无公路,崎岖小道弯曲盘旋,攀壁逾岩筑起的窄窄栈道上的路人,如蚕丛小径,时常担忧崖顶有飞石坠落,脚下有滑坡之危,路塌之险。
我们的车子一路驶去,虽然坦荡平安,但岷江水依然澎湃激荡,如雷贯耳,沿途所见,险滩密布,植被疏落,头顶上的悬崖峭壁,时而飞沙走石跌落、堵塞半截路面,风卷尘沙扑面而来,蔽眼障目。河滩地上,昔日的泥石流滑坡裹挟而下的枯枝、朽木、巨石、风化的变
质岩,杂乱地散布着,像未经清扫的厮杀过的战场。两岸河谷山坡上,羌寨鳞次栉比,伴以过江的索桥,高原的碉楼、关隘、古堡、栈道,时又近黄昏,给人的感觉是奇险苍凉,如入又一个世界。
叶田的镜头始终对准这一切尚未见过的景观。到了藏寨附近的草原上,牦牛群散落于高坡低谷,他干脆要求停车,贪婪地拍摄着眼前的一切。我站在一旁望着他,发现他把镜头久久地对着远方,不由抬头望去,哦,晚霞辉映中,雪峰在远处的山峦之上闪烁着银亮的光辉,悬岩峭壁上,亮崖裸露,那是海拔四五千米之上的寒冽风化所致,大量的岩屑、石块坠积于陡崖的下面,真是难得一见的奇景。
郝师傅说,他已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云遮雾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