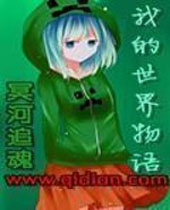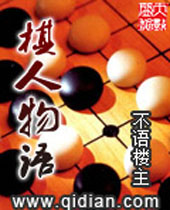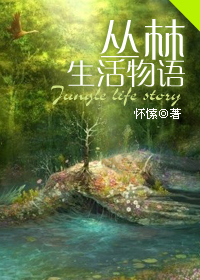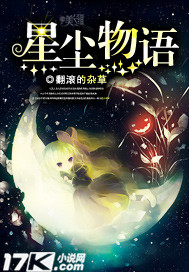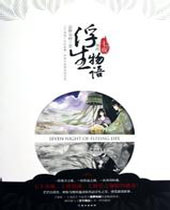后巷说百物语-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正马,你到底想说什么?剑之进不服地说道。
「——到底要我拿出什么证据,大家才愿意相信?」
「稍安勿躁呀,矢作。个人认为令我们质疑的,仅有——惠比寿像的变化和天地变异之间的因果关系罢了。」
这也有理,剑之进不由得开始沉思了起来。
这点应该无法证明罢,正马说道。
为何无法证明?剑之进反问道。
「真的没办法呀,矢作。假设真如传言所述,岛上曾祭有一座惠比寿像。那么,或许真有将神像的脸孔抹红便会发生灾厄的说法流传,也可能有某个不敬之徒将神像的脸孔抹成红色,不,就连不久之后碰巧发生天地变易也是不无可能。但即使如此,仍无法断言这场灾厄是因这起恶作剧而起的罢?」
「你想说什么?」
「这不过是个巧合罢。」正马斩钉截铁地说道。
「巧、巧合?」
「我是如此认为。矢作,稍早你曾言这应非巧合,涩谷也如此附和——但这只能说明此一怪异传言,和这份记录的关系并非巧合罢了。一切天灾均循世间法则而起,哪可能把神佛雕像染红便引起天摇地动?哪管时机再怎么凑巧,地震、海啸、恶作剧和信仰之间,应该还是毫无关连的。凭人的力量——是绝无可能撼动天地的。」
「惠比寿可不是人哪。」
但朱墨是人抹上去的罢?揔兵卫说道。
不,我认为即使端出神佛,道理也是一样,正马继续说道。
「为何也是一样?」
「当然一样。正如涩谷方才所说,除非是先有天灾,事后再捏造个理由解释——两者之间理应不会有任何因果关系才是。因此,我认为除了巧合,别无其他解释。」
嗯,剑之进低声应道。
「再者,就我所听到的,这故事听来实在太像是捏造出来的了。不可亵渎神佛、不可欺骗他人——怎么听都像是在说教。虔诚信神者得救,唯有亵渎神明者殒命——这种情节,怎么听都像是为了拉拢信众而捏造出来的故事。」
「但是,这座神社似乎没有多大哩。」
「是大是小有什么不同?」揔兵卫不甘示弱地继续逼问道:
「只要将过去的惨祸当成神明灵验的证据,对提升当地的信仰应该极有帮助。对一座小神社而言,只要能拉拢当地居民,应该就心满意足了罢。」
「纵使……」
正马继续说道:
「纵使这座岛屿真是因惠比寿的脸孔被抹红而沉没——」
也是绝对无法证明的,正马做出结论。
大概是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剑之进转头望向至今未提出任何异议的与次郎说道:
「与次郎,这些家伙认为你是在吹牛哩。你难道不反驳?」
「不必了——」
他并没有反驳。
剑之进虽然愤慨,但与次郎并不认为自己被人当成是在吹牛。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正马和揔兵卫的推论是正确的。
半个月前。
与次郎在一场酒席上,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这则奇妙的传说。
也就是惠比寿的脸孔转红——导致整座岛屿沉没的传说。
对与次郎而言,这也不过是个随兴聊起的假故事,但正马和揔兵卫强烈否定,剑之进却依然坚信是真有其事,结果就演变成了今天这种局面。说老实话,与次郎并非不相信神佛,但还是不愿相信其神威可能使整座岛屿沉没。
不知大家意见如何——看到与次郎和剑之进的神情,揔兵卫皱了皱眉问道:
「是否该上药研堀找老隐士征询意见——?」
四人先是面面相觑,接着才齐声回答:也好。
【参】
药研堀的隐士——
一如其名,是位居住于药研堀边陲、一户名曰九十九庵的清幽宅邸的老人。
此人年约八十有余,貌似白鹤般细瘦白皙,剪掉了发髻的白发修得短短的,平日身穿墨染的作务衣(注:工作时穿着的服装,上为筒袖,下呈裤状,材质多为蓝色木绵布料。「袖无」是形状如背心的无袖短外套)和深灰色袖无,看来活像个衰老的禅僧。虽不知其出身、姓名,但此人自称一白翁,仅有一名据称为远房亲戚的小女童相伴。
同时,这老人和与次郎曾奉公的前北林藩,似乎曾有段匪浅的交情。
虽然不论怎么看都像个毫无显赫身分地位的寻常老百姓,但藩主对其似乎颇为关照。维新前北林藩曾按月支付恩赏金,每回均由与次郎负责递交。
虽然金额并不算高,但似乎已经支付多年,若论总额,应该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白翁虽然从未向他们提及自己的过去,但与次郎的前上司曾言:「此人是个曾拯救北林藩的大恩人。」
即便北林藩再小,区区一介百姓,而且还是个衰老如枯木的老翁,怎有能耐拯救一个藩国?与次郎虽对此纳闷不已,但这似乎已是与次郎尚未出生的四十数年前的往事了。
如今虽是个老翁,但此人当年毕竟也曾是个小伙子。直到废藩后,与次郎才想到这个理所当然的道理。在此之前,与次郎总有一种此人打从以前起便是个老人的错觉。
因为一白翁看起来已是十分衰老。
五年前,与次郎突然想起这老人,好奇他如今安在?
藩国已随大政奉还而遭到废撤,按理说,他应已不再收到北林藩所支付的恩赏。
若是如此,不知他日子是否还过得去?
因此,与次郎便邀了也曾听说过此老人传闻的揔兵卫,相偕造访九十九庵。
老人依然健在。
虽然已无发髻,但消瘦的脸颊、朴素的生活、以及教人看不出是乖僻还是和善的言行举止,
一白翁看来仿佛仍活在旧幕府时代里。除了与次郎昔日曾见到的远房小女童已成了个年轻姑娘之外,九十九庵里里外外竟是一切如昔。
打从那时起,与次郎便与老人恢复了交情,至今已有五年。如今除了揔兵卫之外,剑之进与正马也常同来造访九十九庵。
老人不仅博学,同时还有过许许多多奇妙的经历。与次郎极爱聆听老人聊起这些意味深长的故事。
维新至今已过了十年。
虽仍偶有动乱,但大致上世间混乱似已暂告平息。只是上自整个国家,下至与次郎均产生了极大变化,街景民情亦已是焕然一新,唯有老人居住的这城中一角仍残存着浓郁的江户习气。对在努力适应新时代的同时,对新事物却仍怀有一丝不信任的与次郎而言,九十九庵的风景、以及一白翁所叙述的江户故事,听来总是如此教人怀念。
虽然身为巡查,但剑之进对奇闻异事却有一股强烈的喜好,尤其酷爱聆听老人所叙述的诸国怪谈。
揔兵卫则是个和他的相貌与职业颇不相符的理性主义者,亦喜爱与老人议论各种不可解之异象。至于略带西洋习气的正马,乍看之下对此类议论问答虽不至于毫无兴趣,但与次郎认为此乃因其对与老人为伴的姑娘小夜颇为钟情使然。
不过,关于这点——与次郎其实也有点可疑——其他两人更是不用说。
买了点豆沙包当土产后,四人便启程前往药研堀。
虽然晚饭时分吃豆沙包是有点奇怪,但由于老人不好饮酒,也不知除此之外还能带些什么。不,正确说来,老人每晚就寝前也会小酌一杯升酒(注:指盛装于名曰升的容器中的酒,或以升盛装贩卖的酒),除此之外,便可说是滴酒不沾了。但这也不代表老人就爱吃甜食——说老实话,这豆沙包其实根本是买给小夜吃的。
透过树篱,一行人瞥见了小夜的身影。
或许她刚洒了点水消暑罢,只见庭院里还摆着杓子与水桶。正马快步跑向门前。「打扰了、打扰了。」还没走到门前,揔兵卫便以粗野的嗓门大喊。与次郎一进门,便看到小夜正坐在玄关旁一只破旧的藤椅上发愣。
咱们又来打扰了,老隐士在么?剑之进问道。也没等小夜回话,正马便递出一包豆沙包打岔道:这是咱们一点心意。
多谢各位厚意,小夜收下豆沙包说道。
该说谢谢的是咱们罢,与次郎回道,紧接着便询问两人是否用过晚饭了。刚刚吃饱哩,小夜回答。三不五时过来叨扰,会不会给两位添麻烦?听到与次郎这么一问,小夜回答:
「哪儿的话?我们也正打算喝杯茶呢。况且,若和各位聊上个一阵,他老人家也会比较精神点儿。」
话毕,小夜便将与次郎一行人请进了门内。
四人没被带往座敷,而是被领到了庭院内的小屋里。
此栋小屋仅约六叠大小,正中央设有一座地炉。虽不见躏口(注:日式茶室的方形入口),但屋内陈设看似一座茶室。老人端端正正地跪坐在壁龛前,老早便摆出了会客的架势。
老人眯起了原本就细小的双眼,一脸看不出是微笑还是不知所措的神情。
「各位全到齐了哩——敢问所为何事?」
「咱们有件事想找老隐士谈谈——」
揔兵卫以粗野的口吻说道,接着剑之进又询问老人近日是否无恙,最后再由正马说几句客套话。这是这伙人每回造访时的惯例。
至于与次郎,通常则是不发一语地跪坐一角。
一伙人一如往常地并肩跪坐,上茶后,剑之进率先开口:
「老隐士,其实今天也没什么事儿,咱们只是打算就与次郎这家伙听说的一则传说之真伪,拜听老隐士的意见。」
请说罢,老人点头说道。
接下来,剑之进便开始向老人陈述瓜生岛的传说。但话还没说几句,便看出老人似乎对这故事颇为熟悉。老隐士也听说过么?正马问道,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呀,老人回答。
「有名么?」
「是呀。虽然濑户内也有类似的故事——」
但应该还是属丰后湾的故事最为有名罢,老人一脸稀松平常地说道。
「濑户内也有同样的传说?」
「老夫当年造访阿波时,也曾听闻类似的故事。总之,这类故事为数颇众。但就规模而言,应该就属瓜生岛这则最大了。毕竟——若老夫记得没错,岛上曾住有上千户人家。」
「上千户?」
「没错,而且记得也不是座贫穷的岛屿。与次郎先生是否听说此处民生困顿?」
在下的确是如此听说,与次郎点头回答。请问可是个年轻小伙子说的?老人又问道。的确是个小伙子,此人要比与次郎年轻个两岁。
「那么,他或许就不知道实情了。在老夫所听说的故事里,将惠比寿的脸抹红的,是个对迷信嗤之以鼻的大夫。想来这也是无可奈何,毕竟是三百多年前的事儿了。」
这故事果真属实?正马问道。
这就不清楚了,老人回答:
「老夫虽然如此年迈,但毕竟也没活过三百年。至于剑之进先生找着的记录,虽为文字记述,但实难论断其中究竟几分为虚、几分为实。」
唔,剑之进拾起放置腿上的文书端详了起来。
「不过——老隐士,倘若连如此记录都不足采信,世上不就无任何东西可信了?」
「世上的确无事可完全采信。」
「但无论如何,事实终究是事实。敢问这座岛——」
「应该是沉没了罢。」
老人如此说道。
剩下的话既然被抢先说了,剑之进也只能默默闭嘴。
「总之,真相究竟如何根本不重要。反正各位也不是来向老夫查证此事的。」
老隐士果然是明察秋毫呀,正马说道:
「方才老隐士不是说,这类故事为数颇众?」
老夫的确说过,老人回答:
「例如,各位是否听说过《今昔物语集》?」
听说过,揔兵卫回答。
「那就好。书中的〈卷第十震旦、卅六〉里头有篇〈媪每日见卒堵婆付血语〉,内容也大致是同样的故事。从震旦两字,不难看出这是个唐土的故事。话说唐土某地有座高山,山顶立有卒塔婆一座。」
「卒塔婆?」
看来这故事果真怪异,听得四人不禁面面相觑。
「山麓下有个村子,村中有个年龄和老夫相若的老躯,每日均不忘上山参拜这座卒塔婆。」
「这座山——高么?」
相当高,被剑之进这么一问,老人便如此回答:
「大家都知道,对年事已高者,登山是件十分艰辛的苦差事。换做老夫,便绝不可能办到。某日,一个小伙子向老躯询问登山的理由,老妪回答传说此卒塔婆若沾上了血,此山必将崩塌并没入海中,因此老妪不得不日日上山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