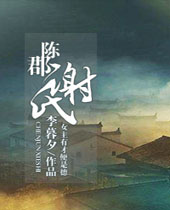陈郡谢氏-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行此大礼,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琅琊公这个称呼,说到底,琅琊郡也不过是江陵下辖荆州八郡之一,他更不是开国郡公,沿袭江陵王爵位,不过从一品之位,俸禄更是拟同二、三品,秩中二千石,让她真正折服的是他这个人本身。
世人都知道,江陵王李陵有两个了不起的儿子,嫡长子李元宏,年二十又五,封清河王;嫡次子李元晔,年十七,封琅琊公。二人少年成名,容貌出众,文采风流,前者十六于范阳登高雅集策论而被时任中正官评为二品,拜大名儒陈郡谢远为师;后者乃是南朝第一名士琅琊王恭的首徒,年方十四便被巡至的太师、太保亲评为一品,以一篇《汾阳集序》技惊四座。九品中正制度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士族子弟但凡入品,必为六品之上。但是,哪怕如此,也鲜少有如此年少之人被评为上三品,更遑论是一品,北朝已有百年未见。此后北地士族皆谓:“江陵李氏有二郎,天下谁人不识君”。
此二人者皆是当世少有的俊彦。
又因其二人仪表俱佳,姿容冠世,有好事者将二人名列北朝四大美男,谓之“江陵二昳”,意为姿容昳丽,无可比拟。
在这个极度崇尚美的时代,女郎妇婆并不掩饰自己对美的喜爱,较之南地,北地风气更浓。传闻李元晔在骊山草堂求学之时,县中乃至临县外郡女郎妇婆每每携闺伴密友来看,三五成群,将个偌大的骊山围得水泄不通,夫子嗟叹,士子怨怼,逼得他不得不移居骊山东南的荒僻险峰,只求一刻安宁。又因其小字檀奴,世人便称其为“江陵檀郎”。
时人皆以貌取人,简直叹为观止。昔年潘岳携弹弓于洛阳城中投射,女郎妇人连手围之,争相赞美,大才子左思想要效仿,结果因为长相丑陋而遭老妪唾弃、老媪投掷。
如此天差地别,叫人忍俊不禁。
元晔回礼:“晔乃庸人,不敢当此重礼。”
元梓桐笑了,挑眉道:“公若为庸人,世间何人敢称士子学士?”
“女郎严重。”
有胡姬进来换盏,撤下空盘,端上一道酱肉片。菜肴是刚刚出炉的,还滋滋冒着热气,色香味俱全,非常诱人。
“君侯先请。”元梓桐笑道。
元晔谢过,执箸欲夹,手却忽然顿在那里。
元梓桐有些心虚,偷看他的神色,佯装镇定道:“有何不妥?”
元晔敛去了眼底藏匿的微笑,坦然食之,只道:“无。只是想起家君远在洛阳,年节之时,唯有大兄、阿母和幼弟在侧,一家人始终无法团聚,不觉心有戚戚。”
元梓桐自小就对他多有倾慕,如今见面,爱意更甚,见他失落不免心有不忍,抚慰道:“令尊人品贵重,忠良贤能,朝野上下无不敬服,素得至尊倚重。此次罹难,定为小人构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身直行,众邪自息。至尊圣明,定然早日查明真相。贵人不必烦忧,尊上不日便可返还。”
“承女郎贵言,晔不甚感激。”他这才释然一笑,原本有些清冷落寞的眸子也多了几分清朗明媚。
元梓桐不敢过于注视他,垂首笑道:“贵人知此,善也。”
外面传来喧哗声,几个衙役打扮的汉子一举掀开帘子,冲进了室内。为首的虬髯汉子衣冠不整,凶相毕露,往门口一站,随意扫视了一圈,冷笑道:“抓起来。”
“安敢无礼?”兰奴上前大喝。
这汉子肆无忌惮地扫了她一眼,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大黄牙:“小娘子,妨碍府衙办公,这可不是好玩的。”
“办公,办的什么公?不说缘由就要拿人?你们是哪里的衙差?”
汉子狞笑一声:“有人举报,这里有人私杀耕牛,取肉而食。至于兄弟是在哪儿办差的,等去了县衙大狱,自然有人会告诉你们。”
兵荒马乱的年代,粮食不易,牛马稀缺,所以朝廷格外重视。自北魏开国以来就有规定不得擅自杀害耕牛马匹,文帝更是在成化三年时颁布过一则条令:“主自杀牛马者,徒二年”。
杀一头牛,关两年啊!
兰奴想起刚才那盘肉,回头去看,李元晔已经起身,对这些衙役道:“我等并不知道这是牛肉。”
那衙役只是冷笑。
兰奴何曾见自家主子受过这等羞辱,怒道:“不说我们没有点这东西,就算吃了,那又如何?你们可知我家公子是谁?”
“王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
兰奴气得七窍生烟,却听身边元梓桐说:“菜是我点的,和他们没有关系,你抓我吧。”
谁知那衙役油盐不进,大手一挥:“抓起来!”
李元晔没有反抗,兰奴当然不能违背她的指令,只能忍着一口气和这个害人不浅的小姑一起被拿了,押送出去。
“娘子,那不是方才灯会上见过的那位公子吗?”出邸舍的时候,锦书忽然指着前方惊呼道。
秋姜停下了脚步。仿佛心有灵犀般,前面那人也侧转过身来。四目相对,他难得地露出了一丝愠怒的神情,面色冰冷,眼底多有嘲色。
秋姜却莞尔一笑,用口型无声地描摹:“*苦短,良缘难遇,望君珍惜。”
第023章 双士对弈
023双士对弈
此后的日子,秋姜一直在院内练习书法。谢衍让人送来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贴,她视为珍宝,每日临摹,不过半月,便略有小成了。
约定出游的日子未到,她却迎来了及笄的日子。
及笄作为古代嘉礼之一,又称“上头礼”,只有贵女行之。秋姜是元妻嫡出,谢衍对这事非常看重,约请了豫州一带不少的名望,又邀了太原王氏的郡君来做正宾,拜帖的不胜枚举,连河南王元瑛都派使者来参礼观礼了。
这日,暖风袭人。一大早,秋姜就被青鸾拉了起来,经过沐浴、熏香等等繁琐的礼序,她已经清醒地不能再清醒。
“过了今日,三娘子便成年了,是大娘子了。”青鸾跪在下座为她换履,笑着道。
锦书附和地点点头,为她换上加礼前的采衣,也是一脸喜气。
翟妪又叮嘱道:“今日来观礼者众多,多为命妇名儒,三娘子切记言行不可有失,以免落人口实。”
秋姜一连声应着,头大如两个:“妪,三娘知晓了,你都说了不下十遍了。”
翟妪无奈地笑了笑。
谢府有八辆牛车,此次出行便备了五辆。祭祀加礼的家庙在郊外东南的葛云山,路途遥远,山路崎岖,多有不便,太夫人想到这点,又让人备了上山乘坐的肩舆,随行的丫鬟婆子也携带了羽扇、如意、方褥、书帛等物,另有仆役小僮抬着器乐和托盘,浩荡而行。
初春时节,外间春光明艳。昨夜下过一场雨,路边的青石台被细雨打湿了,磨得锃光圆滑,映衬树荫底下扶疏的花影,葳蕤的枝叶,恍然如画。
牛车宽敞平稳,甚是舒适。车轮辘辘而响,林间鸟兽清绝。坐了会儿,秋姜拨开轻纱,又让锦书卷起垂帘,对外间跪坐的另一个婢子道:“何时可至?”
答曰:“约一时辰。”
也就是说——还有两个小时?
靠!
秋姜放下帘子,怏怏不乐。车内置有暖炉,时间久了,她不由手心冒汗,身上的采衣黑底朱边,很是繁重,让人燥热难当。翟妪笑道,为她取了香巾擦拭额上的汗珠:“三娘子再忍忍,很快便到了。届时众贤云集,可万万不可失了礼数。”
“诺、诺、诺。”秋姜烦闷地应了多声。
翟妪都被她气笑了。
出了山林,到了葛云山山麓下,秋姜由丫鬟婆子伺候着戴上帷帽,换了肩舆。这下可不比坐着牛车舒服了,人力使力始终各有不同,一路上颠地她摇摇晃晃,好不难受。
锦书在旁道:“你们且稳着些,别摔了我家娘子。”
拉夫们唯唯应着。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秋姜不顾几人的反对下了肩舆,翟妪和青鸾拿她没辙,只好一左一右羽扇为她遮阳。其实这山间林木茂密,哪里来的烈日?秋姜知晓她们性情,也只得由着她们。攀上半山腰,山路愈加奇陡,右侧的林深荫庇处隐约可见寺庙几楹,错落有致。林间香烟袅袅,环绕朱红色的楼宇。
秋姜顿觉神清气爽,又紧走几步,只见庙宇正殿门下有一棵参天大树,树影下有两位跪坐弈棋的士人。
那二人皆是长衫纶巾的儒士打扮,似乎风尘仆仆,许久未修饰,络腮胡子满脸,看不出容貌年纪,只是谈笑间声音颇为清雅悦目。
二人身旁皆有一士子随侍,恭敬站立,目不斜视。秋姜走近了些,发觉这两个少年都颇为俊朗,白衣葛衫,不敷粉黛,虽不及李元晔,却远在当日见过的杨约、杨尹之上。
一人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笑意淡淡,道:“家师对弈,闲人勿扰。”
秋姜并不作恼,却道:“若算机筹处,沧沧海未深。尊师运棋如神,浩博如渊,何惧一小小娘子之陋见乎?”
那执白子的士人闻言抬起头——秋姜对上了一双清澈深远的眼睛,黑如点漆,渊博浩淼,蕴含着难以言说的悠远宁静,仿若与这山间丛林的静谧融为一体,让人无来由地感到一阵清风扑面、神思清明。
秋姜忙欠身道:“陈郡谢三娘,见过尊驾。”
那士人眼中含笑,轻一摆手:“无妨,小姑可上前来观。”
秋姜再拜,恭敬上前,见他二人在棋盘上已对多时,如今是终局较量了。停局填子,子多为胜。这是十九路棋盘,和她前世所学并不相悖,只看一眼,心里便有计较。
对面,那执黑子的士人挥着白玉柄麈尾,朗声笑道:“子封,任你满腹经纶、国士无双,但在这对弈一项上,君输予远矣。”
“子眺骄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执黑子的士人大笑,一双挑花眼微微斜挑,甚是得意,抬头却见面前的女郎盈盈含笑,不置可否的模样,不由挑了挑眉:“小姑有何见解?”
秋姜拱手道:“安敢?”
“但说无妨。”
秋姜低头望了望那执白子的士人,对方也微微含笑,眼神宽厚温和,她心里一定,取了白子往东南角落中一放。
格局立变。
那执黑子的示人不由搁下了麈尾,眉目紧锁,惊疑不定,眸中多有讶异之色。
执白子之士人却略一合掌,笑道:“好一步妙棋。”抬头问她,“小姑师从何处?”
秋姜笑道:“回老丈的话,三娘只是闲暇时候瞎鼓捣玩的,并无师承。”
“老丈?”身边侍立的少年一瞪眼,怒望她,“家师年不过二十又八,何以老丈称之?”
秋姜哑然,却无可辩驳,再低头看跪坐的两人。这满脸胡子的形象,实在看不出不到三十啊!
那执白子的士人却道:“沛云退下。”又见她虽然年幼,生得却是眉清目秀,风姿卓绝,心里不由赞赏,语气愈加温和,笑道:“秋水时至,河伯固于小川,焉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后至北海,方改其观。今日恭方觉吾为井底之蛙,见笑于大方之家耳。”
“竖女岂敢。”秋姜拱手欠身,“先生不必在意,不过是凑巧罢了。”
“小姑聪慧颖悟,不可过于自谦。”
这时方才阻拦她的少年上前恭声道:“师傅,时候不早了。”
两位士人收拾了棋盘,长袖轻甩,踩着木屐扬长而去,姿态洒脱,是秋姜生平仅见。这便是魏晋风流?
这个时代的人非常重视声誉,但并不崇尚那种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像这样洒脱旷达、独立独行的人,才最得世人认可。
翟妪在旁催促她:“女郎,时候不早了。”
秋姜道:“走吧。”
一行众人登上台阶,缓缓步入朱红色的庙门。这是私庙,并不宽敞,广场前后不过二十来丈,置放生池与须弥座若干,彩饰丹垩,栏循台榭,正殿两面的四座钟楼隐于松柏林涛中,隐约可见,庄严肃穆。
场内一应准备就绪,诸像崇严,彩绘鲜艳。秋姜未入殿堂,便见谢衍立于东面台阶上等候宾客,看到她,微微点头,示意丫鬟婆子扶她进侧殿,转头招呼往来宾客。
到了巳时,宾客尽数到场。待下人来禀娘子于侧殿沐浴更衣完毕,谢衍在台阶上高声笑道:“今日诸公拨冗莅临,鄙人不甚荣焉。”说罢,和王氏一齐步下台阶,首先迎接正宾。
王卢氏盛装出席,上裳着紫金缠枝镶边对襟大袖衫,下配丹色、赤金双色条纹裙,外罩薄纱襦袍,容色雍容。
“母亲。”谢衍、王氏皆作揖礼。
王氏乃是庶出,生母虽然早逝,却很受郎主王源器重,年轻时给过王卢氏不少气受,王卢氏自然不待见她。但是,礼数却不能废,虚扶了他们一把道:“勿需置这些虚礼,入内吧。”
王氏扶了她缓缓踏上台阶,谢衍回头招呼其余人,忽然目光凝滞住了。
人群也不由自主分开一条道路。
“谢公,一别多年,别来无恙?”来人白衣翩翩,手执一柄白玉如意,一头乌发并不若其余人那样纶巾或笼冠,而是随意披散在肩上。他的年纪不及三十,姿态却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