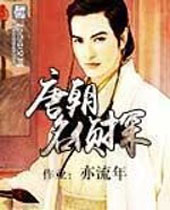塔罗女神探-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源头,方可平安回转。
“这里有,那里也有!”
奶气的童声又在他背后响起,他吓得险些尿出来,所幸一根手指还紧紧卡在刚抠好的墙眼里头,多少缓解了一点紧张。待回过头去,微弱的灯光亦仅仅照到脚面,两边又是茫茫然、黑洞洞的一片。
于是他努力区分幻境与现实,听到的哪些声音是不存在的,哪一些又算真切。为此黄莫如头痛欲裂,暗沉的光线令他两眼酸涩,脚步迟钝,身后仍是鬼魅一般的“噌蹭”作响。
这个辰光,他想起了秦晓满。
她丰艳的唇此刻若正贴住他的耳根,必能消除他现在几近满溢的仓皇。淡薄的酱香掩盖了特殊的土腥气,她可以靠在他怀中,讲一些让两个人都面红耳赤,然而又极渴望的私话……他每每面对她,都像是初识,又似已挨过了一个天荒地老。
迷乱之际,他又摸到一扇暗门,便小心推开,那门依旧哑然地开启,替他保着密。他掩进门内,将煤油灯吹灭,蓦地发现原来自己早已适应了黑暗,周边景物都能看出个大概,甚至还轻松绕过了门边堆放的几只竹编箩筐。
“噌噌”声正不急不缓地逼近,他将暗门留了一道缝,将一只眼睛贴住那缝隙。
来了,终于要来了!
他确定金属声并非幻觉,甚至已看到一团阴影慢慢往那暗门处移动。他屏息窥伺,激动得面孔发紫,但还是将煤油灯抱在怀里,权当是自卫用的“利器”。
虽是在暗无天日的地道,却依旧可以辨认出那黑暗中有个人的轮廓,手中执一长条状的东西,他依稀识别应该是斧头之类的东西,它被来人单手拎住把柄,另一头却在墙上刮擦,遂发出令他心惊肉跳的“噌噌”声。更要命的是,他记起先前在墙上抠的标记,竟被这神秘客一一毁灭,且不费吹灰之力。
经由这一点,他清楚地意识到,此人是奔他而来的!
关乎如何对付跟踪者的法子,黄莫如在暗门背后想了好几个,最后决定等对方走近他掩藏的地方时,突然跳出来,用煤油灯将其砸晕。他从黄梦清那里借来的西洋侦探小说中,已看过太多这样暗算与反暗算的桥段。
打定主意后,他便不再焦躁,只努力贴着门板,等此人近一些,再近一些……斧刃划过墙壁的声音犹在耳后,连泥灰掉落的动静都清晰可辨。他不知为何,竟有些兴奋,隐约怀念起小时候的捉迷藏游戏,寻人的越是靠近藏身地,他便愈是提心吊胆,可一旦对方疏忽了那里,成就感便油然而生。人大抵是天生的“阴谋家”,喜欢算计自己,也算计别人。
来了!真的来了!
他在心里对自己狂叫,灵魂已然发颤发热,玻璃灯罩也快要在手中捏碎。实际上,令他振作的事情还有一件,他已听见对方绵长的呼吸。
只是,那咬人的斧音突然变了,成了“咯哒”,他当下心里凉了半截,因知道那是斧刃擦在他藏身的暗门上发出的动静,这扇门,到底还是出卖了他!
他亦是豁出性命一般,猛地将门打开,高高举起煤油灯。刚一抬头,却已绝望。只见对方的利斧已举在他的头顶,下劈速度之快,犹似劲风扫过,同一时刻,他仿佛听见了死神的召唤……
【3】
夏冰的笔记本上已画得密密麻麻,杜春晓对画画一窍不通,所以线条曲曲扭扭,只能勉强看出个意思来。这是他们第五次摸进密道,可谓经验丰富,夏冰还借了顾阿申的手电筒,只可惜太过费电,不如火折子烧得久,于是后来竟将灯笼也带去了,蜡烛火柴也备了一些。杜春晓还拿炭笔在每个门上做记号,代表已经进去过了,并标出那里通往何处。
不过很快,他们便发现,下一次进密道的时候,门上墙上的炭笔记号都已被擦掉了,可见里头还有别的人,于是忙四处乱跑一通,想“捉活的”,可底下复杂如迷宫,东南西北都不知道,哪里还有能力追踪某个人。用杜春晓的话来讲:“宝是挖到了,只可惜带不走,赚不到钱。”
那些日子里,李常登也是忙乱的,将简政良的房子盘下以后,忙着把钱藏到安全处,更是借办案的名义,忙着进出黄家。张艳萍每回都是呆滞着一张脸招呼他,他却能从她枯萎的姿容里看出曾经的风华,如今她就像某件“纪念物”,只是蒙了灰,且被岁月磨蚀过了。但也由此,他对她的恋情,竟比年少时还要坚硬一些,这令他觉得安稳。
“你可记得我?”
因有下人在旁,他问得尤其隐晦,装作只是随意试探一下她的病情。
她抬起一双茫然的眼,望着窗外那蓬金盏花上一掠而过的灰雀,头发里散发的异味儿表示她已许久不曾受过悉心照顾,嘴唇起着倒皮,十片指甲都是秃的,皮肤上的纹路经纬分明,周身上下的那股子寥落,仿佛直接被打上了“失宠”的烙印。阿凤更是无精打采,倚在桌子旁绣一个香包,每下几针便打一个哈欠,起初对李常登来访亦是诚惶诚恐的,次数多了,热情也便消了,只懒懒端茶上来了事,连续水的活都不屑做。
“等我,不消多久了!”
李常登将手中的菊花茶一气喝尽,自心里对张艳萍许下一个承诺,茶水的清甜凝成一滴苦泪,由眼角沁出,他胡乱用手掌抹了一把脸,便走出去了。
张艳萍仍是静坐在那里,宛若一座尘封住的残破雕像,阳光从她脸上轻盈地跃过,不留一丝暖痕。
佛堂内的祖宗牌位已被擦得快要脱一层壳,因黄天鸣是白手起家的孤儿,自己父母姓甚名谁都不晓得,所以祭的祖实是孟卓瑶娘家的人,包括她的父母、外公外婆,还有一位据说活过百岁的太公。佛堂虽大,只这几只牌位也确是寒碜了些,可明眼人都晓得,立下这样的规矩传统绝非一时兴起,而系黄天鸣的交际门道,要想家业稳固,无非人脉根基打得好,由此生意兴旺,一帆风顺。
家中虽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孟卓瑶却显得尤其清闲,正坐在女儿屋里吃茶。黄梦清知她必要发一通牢骚,忙叫玉莲拿出些香瓜子来,以供母女二人聊天。
“依我看,母亲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享清福,何须劳这样的心?二娘做得再好,还不是为母亲做的,难不成您都忘记了咱们要祭拜谁的牌位?”
黄梦清少不得这样劝慰。
孰料孟卓瑶却摇头道:“有些事情你们小的是不知道的,自古大家宅里总是要出些祸害,你以为这里没有么?还不是老爷色迷心窍,只看到我的不好,看到别人的好。”
说毕,眼中掠过一丝凄凉。
正说着,却见玉莲急匆匆进来禀告:“杜姑娘来了!”
黄梦清先是一惊,遂摆出恼怒的神色来,只道:“且叫她进来,倒要问问她这几日是到哪里开坛作法扮神婆去了。”
话音刚落,杜春晓人已自顾自跑进来,嘴里只喊渴,要喝茶。孟卓瑶哭笑不得,说道:“你说杜姑娘如今,倒像是我们家的人,只不知当她女儿好呢,还是下人好。”
“不像女儿,更不像下人,而像咱们的老祖宗,要这么样服侍着。”黄梦清这一句,将在场的几个人均逗笑了,唯杜春晓没心没肺地只顾喝凉茶,完了还长长叹了一大口气。
黄梦清见她脸上身上都是泥,皱眉道:“看来不是去做神婆,倒是去种地了,脏成这样。”
杜春晓拿手背擦了擦嘴巴,笑道:“不是去种地,是去玩了通更神奇的把戏!”
“什么把戏?”孟卓瑶好奇心重,便急着问了。
“过几日再与你们细说,如今要保密的!”
黄梦清已笑得直揉肚子,嘴里叫着“唉哟”,孟卓瑶也一扫先前的阴郁,整个人都舒展开了,屋子里原本幽怨的气氛瞬间无影无踪。
※※※
张艳萍不晓得睡了多久,只知睁开眼的时候,浑身无力,动一根手指都是难的。甚至搞不清眼睛究竟有没有睁开,因捕不到一丝光线,周身似沉入一片黑海,摸不到什么边际。想开口叫茶,又觉得口鼻处闷闷的,面部每一条肌肉均被拉扯到极限。口腔里塞了一个滚圆的硬物,将舌头强行压住,她强迫自己发声,却只听见“呜呜”的闷叫,方发觉自己嘴上被布条之类的东西封住了。当下想坐起来,手臂却一阵酸麻,且是一直贴在臀部上的,腕部像是被一种坚韧的细绳缠紧了,脚踝也是,以至于翻身的辰光能痛出眼泪来。
她不晓得自己在哪里,是谁抓的她,只能缩在这个深渊里等待被救。只是谁会来救她呢?在众人眼里,她如今不过是个疯婆子,黄家的累赘、废物,唯一的价值无非是给了黄天鸣娶四姨太的理由。但她仍在坚持,李常登深情苦楚的眼神给了她信心,令她对这样前途凶险的抉择无比执著。明知装疯是要从此入魔道,经受阿鼻地狱考验的,她却以为这是唯一能挽回事态的方法。
可现在,这个本该消除了所有人戒心的疯婆子,却被捆得像只粽子,她直觉被绳子勒住的皮肉正在溃烂流脓,一股淡淡的腥臭抚过鼻尖。她心情沮丧地挣扎了一下,喉咙里又“呜”了一声,依旧无人回应。
她终于有些急了,顾不得疼痛,将整个身子奋力扭动,被反剪的双手突然重重擦过一条坚硬的边沿。她无助地堕落,灰尘即刻涌入鼻腔,她想咳嗽,却怎么也做不到,只是在看似地面的地方来回翻滚,一对被强行绑拢的金莲竭力向外伸张,期望能触到一些东西,抑或一条生路。
一道炽黄的光芒在张艳萍身后燃起,她知道有人在这里点了灯,既喜又怕,欲折转身子将来人看清楚,可很快便打消了念头,只僵在原地不动。因她想到,倘若看清这歹徒的面目,保不齐会被杀人灭口,勿如这样继续装疯卖傻,也许能留条命也未可知。
可那人似乎并不了解张艳萍的苦心,反而将她的身子掰过来,于是两人便不得不正面相对。张艳萍看到的是个罩着黑色斗篷的人,整张脸,整副身体均被那斗篷掩埋起来了。她于是猜想此人可能是镇民一直传说的湖匪,将她绑了去勒索赎金的,想到这一层倒反而安心了些,因知自己一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万一不是呢?
这念头几乎要将她折磨成真疯子。
正在挣扎之际,那人已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拉起,她只好直起身子,也借机观察了一下环境,竟是间没有窗户的空间,四四方方,除门边放着一张板凳之外,别无他物。
她当即有些绝望,心想若真要在这里待上几天,怕是比死还要难过。绑她的人却似乎没什么顾虑,只拿一张绳索绕在她脖子上,在后颈处打了一个活结。她复又惶恐起来,拼命摇头,两眼溢满泪水。对方动作干净利落,看起来镇定得很,似乎一切都只是依照计划执行,没半点迟疑。她的恐惧此时却已抵达制高点,尤其那条套在颈上的绳索慢慢拉长,被系于一只生锈的墙钉上时,她两只裤管里已淌下腥臊的流热。
对方对张艳萍的失禁视而不见,只顾做自己的事,将门边的凳子拿到屋子中间,然后站上去,把连系着她脖子的绳索与顶部的一根横木绑在一道,此人每用力打一个结,她的脖子便被抽紧一次,空气流过愈渐窄小的喉管,变得珍贵无比。
待那人把张艳萍托上那只凳子的时候,她才晓得自己的死法,只要凳子一倒,她的脖子便也应声而断。所以她只得在绝望中保持平衡,将脚下那只攸关生死的凳子踩稳,但她明白,只要这个看不清面目的人轻轻将凳脚一勾,她便要走上奈何桥。因此她双目暴睁,死死盯住对方,接下来的任何一刻,都极有可能是她的末日。
也不知过了多久,对张艳萍来讲,可算是经历几个世纪,凳子没有倒地,她也未曾听见自己脖子断裂的声音。那位神秘客只是拿起灯笼,背转身走出去了,顺带还关上了门。
她旋即又被沉入了“黑海”。
【4】
黄莫如疯狂地往前跑,每跑几步便敲击一下墙面,希望能找到一道暗门,好让他绝处逢生。虽已大致看得清周围形势,可到底是在摸黑,恐惧感从未消失过。脚下踩到的东西发出熟悉的“噗噗”声,地面开始变得干燥,较先前走过的湿地要好一些,他没有放松警惕,只顾奔逃,因怕先前那个握着斧子的杀手会爬起来继续跟随他,并伺机要他的命。他有些记不得自己是如何逃脱对方的斧子的,只知当时周围都是黑雾,唯斧刃边缘是雪亮的,他已无路可退,只得大吼一声,扑过去抱住对方的腰。那人因这突如其来的冲力,仰面倒下,两个人滚在一起,黄莫如用煤油灯狠狠敲击对方,他看不清究竟打在了哪里,只知对着身下奋力扭动的活体进攻……
那个辰光,他已经不害怕了,周身反而散发出杀气。原来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确是会不顾一切地自保。尽管他已听到斧头落地的声音,亦丝毫没有放松,唯一的念头便是要让这“怪物”不动,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