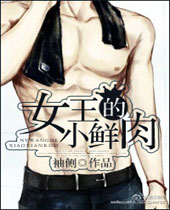孩子王-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递给我。我翻开一看,是一本奖给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本子,上写奖给“王七桶”。我心里“呀”了一声,这王七桶我是认识的。
王七桶绰号王稀屎。稀屎是称呼得极怪的,因为王七桶长得虽然不高,却极结实,两百斤的米包,扛走如飞,绝不似稀屎。我初与他结识是去县里拉粮食。山里吃粮,需坐拖拉机走上百多里到县里粮库拉回。这粮库极大,米是山一样堆在大屋里,用簸箕一下下收到麻袋里,再一袋袋扛出去装上车斗。那一次是两个生产队的粮派一个拖拉机出山去拉。早上六点,我们队和三队拉粮的人便聚来车队,一个带拖斗的“东方红”拉了去县里。一上车,我们队的司务长便笑着对三队的一个人说: “稀屎来了?”被称作稀屎的人不说话,只缩在车角闷坐着。我因被派了这次工,也来车上坐着,恰与他是对面,见他衣衫破旧,耳上的泥结成一层壳,且面相凶恶,手脚奇大,不免有些防他。两个队的人互相让了烟,都没有人让他。
我想了想,便将手上的烟指给他,说:“抽?”他转过眼睛,一脸的凶肉忽然都顺了,点一点头,将双手在裤上使劲擦一擦,笸箩一样伸过来接。三队的司务长见了,说:“稀屎,抽烟治不了哑巴。”大家都笑起来。我疑惑了,看着他。他脸红起来,摸出火柴自己点上,吸一大口,吐出来,将头低下,一支细白的烟卷像插在树节上。车开到半路遇到泥泞,他总是爬下去。一车的人如不知觉一般仍坐在车上。他一人在下死劲扛车帮,车头轰几下,爬上来,继续往前开,他便跑几步,用手勾住后车板,自己翻上来,颠簸着坐下。别人仍若无其事地说笑着,似乎他只是一个机器部件。出了故障,自然便有这个部件的用途。我因不常出山,没坐过几回车,所以车第二次陷在泥里时,便随他下车去推。车爬上去时,与他追了几步。
他自己翻上去了,我没有经验,连车都没有扒上。他坐下后,见我还在后面跑,就弓起身子怪叫着,车上人于是发现,我喊叫起来,司机停下车。他一直弓着身子,直到我爬上车斗,方才坐下,笑一笑。三队的司务长说:“你真笨,车都扒不上么?”我喘息未定,急急地说:“你不笨,要不怎么不下车呢?”三队的司务长说:“稀屎一个人就够了嘛!”车到县里,停在粮库门前。三队来拉粮的人除了司务长在交接手续,别的人都去街上逛,只余他一人在。我们队的人进到库房里,七手八脚地装粮食。装到差不多,停下一看,那边只他一人在装,却也装得差不多了。
我们队的人一袋一袋地上车,三队却仍只有他一人上车。百多斤的麻袋,他一人扛走如飞。待差不多时,三队的人买了各样东西回来,将剩下的一两袋扔上车斗,车便开到街上。我们队的人跳下去逛街,三队的人也跳下再去逛街,仍是余他一人守车。我跳下来,仰了头问他:“你不买些东西?”他摇一摇头,坐在麻袋上,竟是快乐的。我一边走,一边问三队的司务长:“哑巴叫什么?”司务长说:“王七桶。”我问:“为什么叫稀屎呢?”司务长说:“稀屎就是稀屎。”我说:“稀屎可比你们队的干屎顶用。”司务长笑了,说:“所以我才每次拉粮只带他出来。”我奇怪了,问: “那几个人不是来拉粮的?”司务长看看我,说: “他们是出来办自己的事的。”我说:“你也太狠了,只带一个人出来拉一个队的粮,回去只补助一个人的钱。”司务长笑笑,说:“省心。”
我在街上逛了一回,多买了一包烟。回到车边,见王七桶仍坐在车上,就将烟扔给他,说:“你去吃饭,
我吃了来的。”王七桶指一指嘴,用另一只手拦一下,再用指嘴的手向下一指,表示吃过了。我想大约他是带了吃的,便爬上车,在麻袋上躺下来。忽然有人捅一捅我,我侧头一一看,见王七桶将我给他的烟放在我旁边,烟包撕开了,他自己手上捏着一支。我说:“你抽。”他举一举手上的烟。我坐起来,说:“这烟给你。”将烟扔给他。他拿了烟包,又弓身放回到我旁边。我自己抽出一支,点上,慢慢将烟吐出来,看着他。逛街的人都回来了,三队的司务长对王七桶说:“你要的字典还是没有。一”王七桶“啊、啊”着,眼睛异样了一下,笸箩一样的手松下来,似乎觉出一天劳作的累来。司机开了车,一路回到山里,先到我们队上将粮卸了,又拉了王七桶一队的粮与人开走。我扛完麻袋回到场上,将将与远去的王七桶举手打个招呼。
我于是知道王福是王七桶的儿子,就说: “你爹我知道,很能干。”王福脸有些红,不说话。我翻开这个本子,见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独个的字,便很有兴趣地翻看完,问王福: “好。有多少字呢?”
王福问: “算上今天的吗?”我呆了一下,点点头。
王福说: “算上今天的一共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
我吃了一惊,说: “这么精确?”王福说: “不信你数。”我知道我不会去数,但还是翻开本子又看,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字你算十个字吗?”王福说: “当然,不算十个字,算什么呢?
算一个字?”我笑了,说: “那么三千四百五十一便是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了?”王福没有听出玩笑,认真地说: “十字后面是百、千、万、亿、兆。这兆字现在还没有学到,但我认得。凡我认得而课文中没有教的字,我都收在另一个本上。这样的字有四百三十七个。”我说: “你倒是学得很认真。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学了多少字呢。”王福说: “老师当然学得多。”这时钟响了,我便将本子还给王福,出去回到办公室。
老陈见我回来了,笑眯眯地问:“怎么样?还好吧?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那个,一下就会习惯的。”我在分给我的桌子后面坐下来,将课本放在桌子上,想了想,对老陈说:“这课的教法是不是有规定?恐怕还是不能乱教。课本既然是全国统一的,那怎么教也应该有个标准,才好让人明白是教对了。比如说吧,一篇文章,应划几个段落?段落大意是什么?主题思想又是什么?写作方法是怎么个方法?我说是这样了,别的学校又教是那样。这语文不比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世界上哪儿都是统一的。语文课应该有个规定才踏实。”老陈说:“是呀,有一种备课教材书,上面都写得有,也是各省编的。但是这种书我们更买不到了。”我笑了起来,说:“谁有,你指个路子,我去抄嘛。”老陈望望外面,说:“难。”我说:“老陈,那我可就随便教了,符不符合规格,我不管。”
老陈叹了一口气,说: “教吧。规定十八岁人才可以参加工作,才得工资,这些孩子就是不学,也没有事干,在这里学一学,总是好的。”我轻松起来,便伏在桌上一课一课地先看一遍。
课于是好教起来,虽然不免常常犯疑。但我认定识字为本,依了王福的本子为根据,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实。语文课自然有作文项目,初时学生的作文如同天书,常常要猜字到半夜。作文又常常仅有几十字,中间多是时尚的语句,读来令人瞌睡,想想又不是看小说,倒也心平气和。只是渐渐怀疑学生们写这些东西于将来有什么用。
这样教了几天,白天很热闹,晚上又极冷清,便有些想队里,终于趁了一个星期天,回队里去耍。老黑见我回来,很是高兴,拍拍床铺叫我坐下,又出去喊来往日要好的,自然免不了议论一下吃什么,立刻有人去准备。来娣听说了,也聚来屋里,上上下下看一看我,就在铺的另一边靠我坐下。床往下一沉,老黑跳起来说:“我这个床睡不得三个人!”来娣倒反整个坐上去,说:“那你就不要来睡,碍着我和老师叙话。”大家笑起来,老黑便蹲到地下。来娣撩撩头发,很亲热地说:“呀,到底是在屋里教书,看白了呢!”我打开来娣伸过来的胖手,说: “不要乱动。”来娣一下叫起来:“咦?真是尊贵了,我们劳动人民碰不得了。告诉你,你就是教一百年书,我还不是知道你身上长着什么?哼,才几天,就夹起来装斯文!”我笑着说:“我斯文什么?学生比我斯文呢。王七桶,就是三队的王稀屎,知道吧?他有个儿子叫王福,就在我的班上,识得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第一节课我就出了洋相,还是他教我怎么教书的呢。”
大家都不相信,我便把那天的课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真的,咱们识得几个字呢?谁数过?”我说: “我倒有一个法子。我上学时,语文老师见班上有同学学习不耐烦,就说:‘别的本事我不知道你们
有多大,就单说识字吧。一本新华字典,你们随便翻开一页。这一页上你们若没有一个不会读、书、解的字,我就服。以后有这本事的人上课闹,我管我不姓我的姓。’大家不信,当场拿来新华字典一翻,真是这样。瞧着挺熟的字,读不出来;以为会读的字,一看拼音,原来自己读错了;不认识,不会解释的字就更多了。大家全服了。后来一打听,我们这位老师每年都拿这个法子治学生,没一回不灵的。”大家听了,都将信将疑,纷纷要找本新华字典来试一试,但想来想去没有人有字典,我说我也没有字典,大约还是没有卖的。来娣一直不说话,这时才慢慢地说:“没有字典,当什么孩子王?拉倒吧!老娘倒是有一本。”我急忙说:“拿来给我。”来娣脸上放一下光,将身仰倒,肘撑在床上,把胖腿架起来,说:“那是要有条件的。”大家微笑着问她有什么条件。
来娣慢慢团身坐起来,用脚够上鞋,站到地上,抻一抻衣服,拢一拢头,向门口走去,将腰以下扭起来,说:“哎,支部书记嘛,咱们不要当;党委书记嘛,咱们也不要当,也就是当个音乐老师。怎么样?一本字典还抵不上个老师?真老师还没有字典呢!”大家都看着我,笑着。我挠一挠头,说:“字典有什么稀奇,可以去买,再说了,老陈还不是有?我可以去借。”来娣在门口停下来,很泄气地转回身来,想一想说:“真的,老杆儿,学校的音乐课怎么样?尽教些什么歌?”我笑了,把被歌声吓了一跳的事讲述了一遍。来娣把双手叉在腰上,头一摆,说:“那也叫歌?真见了鬼了。我告诉你,那种歌疆叫‘说’歌,根本不是唱歌。老杆儿,你回去跟学校说,就说咱们队有个来娣,歌子多得来没处放,可以请她去随便教几支。”我说:“我又不是领导,怎么能批准你去?”来娣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写个词,我来作个曲。你把我作的歌教给你们班上的学生唱,肯定和别的班的歌子不一样,领导问起来,你就说是来娣作的。领导信了我的本事,笃定会叫我去教音乐课。”大家都笑来娣异想天开。我望望来娣。来娣问: “怎么样?”我说:“可以,可以。”老黑站起来说:“什么可以?作曲你以为是闹着玩儿的?那要大学毕业,专门学。那叫艺术,懂吗?艺术!看还狂得没边儿了!”来娣涨红了脸,望着我。我说:“我才念了几年书,现在竞去教初三。世界上的事儿难说,什么人能干什么事真说不准。”来娣哼了一声说:“作曲有什么难?我自己就常哼哼,其实写下来,就是曲子,我看比现在的那些歌都好听。”说完又过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一拍我的肩膀:“怎么样,老杆儿?就这么着。”
出去搜寻东西的人都回来了,有于笋,有茄子、南瓜,还有野猪肉干巴,酒自然也有。老黑劈些柴来,来娣支起锅灶,乒乒乓乓地整治,半个钟头后竟做出十样荤素。大家围在地下一圈,讲些各种传闻及队里的事,笑一回,骂一回,慢慢吃酒吃菜。我说:“还是队里快活。学校里学生一散,冷清得很,好寂寞。”来娣说:“我看学校里不是很有几个女老师吗?”我说: “不知哪里来的些斯文人,晚上活着都没有声响。”大家笑了起来,问:“要什么声响?”
我也笑了,说:“总归是斯文,教起书来有板有眼,我其实哪里会教?”老黑喝了一小口酒,说:“照你一说,我看确是识字为本。识了字,就好办。”有人说:“上到初三的学生,字比咱们识得多。可我看咱们用不上,他们将来也未必有用。”来娣说:“这种地方,识了字,能写信,能读报,写得批判稿就行,何必按部就班念好多年?”老黑说:“怕是写不明白,看不懂呢。我前几天听半导体,里面讲什么是文盲。我告诉你们,识了字,还是文盲,非得读懂了文章,明白那里面的许多意思,才